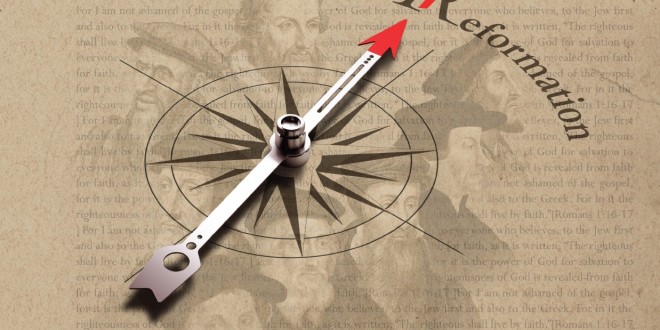文/本刊编辑部
编者按:在今天的信仰生活中,我们应当如何认识宗教改革?如果通过改教家和他们的著作来分析出宗教改革的精髓,又如何应用在今日教会的宣讲和牧养中?我们邀请了五位平日比较关注宗教改革神学的牧者一起来畅谈这些问题。他们首先谈了自己与宗教改革“相遇”的经历,宗教改革在哪些方面影响了他们的信仰和事奉;其次谈到了在教牧现场和神学学习中,他们所观察、感受到的,当代教会与宗教改革“相遇”时要面对的议题。本文整理自该座谈会的录音,文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宗教改革与我”,结合经历的分享提出五个议题;第二个部分是“以宗教改革精神五问当代教会”,初步讨论和回应这五个议题。
宗教改革与我
提摩太——
我刚开始了解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的《论意志的捆绑》读了不下两遍,但是那时对于宗教改革的全貌没有概念。对于因信称义,也只是接受了这个结论,而没有更自觉地深入学习。那么为什么我现在试图更加关注宗教改革呢?一个原因是,我们是在神历代的百姓的传承当中来认识真道,所以我也希望通过重新认识宗教改革运动和之后的传承过程,能够知道真道是怎样传下来的。另一个原因是,宗教改革是在当时的背景下试图要改革天主教会,并进而走向与之分离,而从我了解到的一些资料、动向,好像今天教会却试图又回到与天主教的合一当中去。因此我觉得有必要了解当时分离的原因,来看今天我们作为“宗教改革的后裔”,怎么面对当代教会整体的一些动向和趋势。
我觉得宗教改革对于当代福音派教会的影响,比较明显地趋于淡化了。暂且抛开宗教改革讨论的神学要点、具体内容,宗教改革有两个明显的外在特征:第一个是争论,第二个是分离,就着教义的细微争论和与天主教的分离,而这两个在当代都是被淡化的。淡化教义的争论,不是坚持分离,而是试图跟天主教合一。
提出问题1:我们现在试图淡化宗教改革,趋向与天主教合一吗?其中隐含着怎样的危机?
岩铎——
未信的时候,我印象中的马丁•路德是一个改革家,是开始了德国文化的人——德国人从马丁•路德改教开始,有了文化上的自觉,而且是通过马丁•路德开始正确地说德语。而作为基督徒,我最初接触宗教改革竟然是通过一本异端的书。其中跟宗教改革有关的有三件事。一个是读经,书中引用了马丁•路德所说的一段话,而我把这段话写在了自己的读经笔记本上,就是“你千万不要以为凭自己的智慧能读懂圣经,必须是圣经的作者自己教导你,就是圣灵。……你应该相信我的话,因为你知道我在这方面是有实际的经历的。”这段话导致我每次读经之前都祷告。另一个有关自由。书中说,因为宗教改革发现了圣经,也发现了神在福音里赐给人的自由,所以就脱离了天主教的繁文缛节对人的压制。第三个是清洁。就是宗教改革要清除掉所有的人为加到神百姓的教会生活、日常生活中的那些东西。
后来读神学的时候,我开始读《基督教要义》,它让我对圣经的教义形成一种整体性的知识了解。我知道这些都是正确的,但这些正确的内容对我并没有构成动力。
我对宗教改革真正产生某种自觉,应该是从2002年开始的。当时一位老师讲教义史的时候重新讲马丁•路德的改教,并且强调他建立了更正教会的信仰基础,也把宗教改革的成果和现在流行的说法作比较。我开始形成自觉的神学分辨力。当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三个方面。一是马丁•路德的祈祷、试炼、默想和十字架神学的方法论。二是把重点放在神的行动上,这点给我的触动很大。这位老师说,我们很强调人向神的转回,但是在救恩的行动中所发生的最惊人的事情不是人向神转回,而是神为了“转回”而设立挽回祭,并通过挽回祭神向人转回。这就是耶稣工作的要点——使向我们忿怒的神,因着耶稣的挽回祭而成为向我们施行拯救、称我们为义的神,其中的关键是神向我们转回。第三,这位老师比较细致地分析了马丁•路德的称义论和天主教的称义论的差别:什么是归算式的称义,什么是注入式的称义;经过他的仔细分析就可以知道这两个称义论的差异是根本性的。这使我当时对称义论理解不够清晰的部分清晰了。
此后马丁•路德的著作给我帮助最大、影响也最深的就是《论意志的捆绑》。我发现宗教改革中有极深刻的基于生存性的关注,不是社会性的,不是文化性的,不是政治性的,甚至也不是关于圣洁生活的,而是生存性的关注,就是对得救的关注。我一定要说今天的教会跟宗教改革时期有一个极重大的差别就是缺乏这个关注,甚至在这点上我们都不如当时的天主教;当时的天主教也关注这个问题,但是给出的答案是错误的,而我们现在是不关注这个问题,使正确的答案落了空。
在马丁•路德的神学里,我也学到圣经是神的话,是活的。过去从解经的意义上,我了解“神的话是行动的”这个概念,但是对于福音究竟是怎样行动、构成了解圣经众多真理的切入点和出发点,我并不知道。而马丁•路德却强调圣灵怎样藉着道、在神的时候工作,神通过行动创造事实,通过话语建立事实,这些重新构成我对福音的了解,就是“神活的话”。马丁•路德教我:福音不是对神行动的传讲,福音就是神的行动。
另外,十几年来作为牧者我有一个焦虑,就是对基督徒而言真正决定性的那个实在,究竟是这个世界中可见、可以衡量、信的人和不信的人共有的部分,还是不可见、不可触及和理解、唯独信的人因信福音而有的那个实在、那个事实。这个实在是超越的,还是在所有人的共有经验中?在学习马丁•路德的著作中,这个问题的答案变得清晰,真正的实在(Reality)是凭信心,不是凭眼见,是在福音里藉着信心才能进入的事实。比如说,教会是什么?你可以说教会是一个社团,有着共同的信念,按照某种约定在一起,有共同的行为模式,因此也有一般社会性的权利和责任。你也可以完全不管这些,只看教会是因着神怎样的行动造成的,又因着神怎样的行动在继续成长,又因着神怎样的行动是活着和有价值的。这是非常不一样的思路,我觉得能产生这样超越的对信仰生活的认识,都跟马丁•路德的改教有关。
在这个过程中,我反而发现,原来读的《基督教要义》中那些理所当然以为正确的道理活泼起来了。我常常觉得加尔文主义者一定要读读马丁•路德,加尔文主义才能成为活的加尔文主义。加尔文自己是读马丁•路德的,甚至加尔文在对某些问题的说明中几乎是完全照抄马丁•路德的几个要点,只是他很会整理,更简洁、清晰、条理分明,但是因为缺乏论战性,就缺乏读马丁•路德时有的那个动态的感受。所以,为什么改教那么强大的教义在我们心里不引起波动,我想是因为我们领受它时,没有使加尔文激动的那个动力。如果我们也像改教家们那样,面对着马丁•路德的福音再发现、再确认和整理教义的过程,那么教义对我们也会很有活力。
提出问题2:宗教改革的核心精神是什么?当初改教家们关切的核心问题,今日教会还关注吗?
瓦器——
对于“宗教改革和我”这个问题,我想到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个人在得救的历程当中,怎么去认识宗教改革所说的福音;另一个是我对宗教改革神学的接触以及反思。其实这两方面也很难分开,因为神学上的反思与我个人得救、事奉的经历是在一个互动的过程当中。
首先,我确切地体会到宗教改革所说的福音,是我体会到“称义”之时。记得刚信主的时候,我特别感受到与罪的争战。我不停地犯罪,同一样罪不停地犯,这让我非常痛苦,我该怎么来到神的面前?每次犯罪之后,我特别能体会到耶稣是为我这样一个可恶、肮脏的罪人死,他为我流血,使我能够靠着他“厚着脸皮”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祈求神的怜悯。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犯了罪,神反倒因为基督恩待我,甚至竟没有按照我所预期的来管教我。这是在初信的时候,福音带给我的强大冲击。
不久后,我所在的教会就展开了以预定论为标志的改革宗神学,和以敬虔主义或者说传统家庭教会倪柝声思想为标志的神学的“交通”。在信仰生活当中,其实我长期以来受敬虔主义影响(因为我的带领人受倪柝声思想影响,他以这样的进路带领我祷告,教导我认识十字架的路),而我却同时又读到一些关于加尔文主义的文章,这在我的生命中引起很大的冲突。例如,我记得带领人对我说过,神恩待你、使用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看重你向着他的心,或看重你的单纯真诚等等。可是我当时受加尔文的影响,认为就自己本相的败坏而言,没有丝毫可被神看重的地方。
我初信时的这个经历,没想到后来成为我们教会的路线之争,事实上这种神学的不同导致了教会的分裂。在教会的分裂中,我开始更多神学上的反思。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怀疑以预定论为中心的这类教导,我觉得好像形成了一种非常机械的关系。直到后来我读了巴刻的《生命的重整》,对于神的恩典和人的行为之间的关系才清晰起来,明白了人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是神恩典和工作带来的结果。
其实现在看来,当初造成教会分裂的真正原因是我们刚刚开始建立信仰告白时,在神学上有一些东西是模糊的(例如什么时候可以称“在神的预定中”,什么时候应该说“在神的护理中”),没有清晰、透彻,再加上一种强硬的态度就导致了教会的分裂。因为这样的经历,后来我在学习教义的过程中越来越深地感受到:为什么宗教改革开始的时候,福音的冲击力是那么大,而同样传承下来的教义今天在教会中却没有那么大的冲击力呢?宗教改革时期讲到教义的时候,每一个教义是清晰、活泼地体现在人的生命历程和教会事奉中,而今天的教会里,教义更多是抽象、不容易接受和理解的;所以我们虽然花了很多时间来教导教义的内容,但信徒所得到的只是抽象的知识,在实际生活当中他们自发的关注还是该做哪些事、如何做。他们很热心地做事,学习不少知识,但是行为中所体现出来的,并不是因着学习教义而带来的强有力的回应,教义并没有真正地来塑造他们的生活。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也许是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懂这些教义。教导教义的人,在理论上可能有一个完整的表达,但是对于教义在实际生活中该怎样活泼地应用,仍然是陌生的。所以我们对于教义的教导是灌输式的,弟兄姐妹实际的反应自然跟不上。
提出问题3:为什么宗教改革开始的时候,福音的冲击力如此之大,而同样传承下来的教义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却似乎没有那么大的冲击力呢?
杖恩——
我是以预定论为接触点,开始了解宗教改革的。从预定论中,我看到神是不能够随便对待的一位,而救恩黑白分明,非常需要去搞清楚。当时我刚刚信主不久,为了弄明白怎么信才算数,就开始读《基督教要义》,收获挺大。
我真正读马丁•路德是在两年以后。那时候我经历一些事情,对于得救确据当中的另一些问题感到困惑,同时也开始关心与“神的工人的认定”相关的问题。《加拉太书注释》、《这是我的立场》对我帮助都很大。特别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认识论方面:我怎么知道我所认识的就是对的,从纯理性的角度来看这是无解问题,这也是当时天主教质问马丁•路德的问题。还有一个方面是事奉神的人的权柄(这两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延伸)。读了这些书之后,我对宗教改革的看法改变了,我以前觉得宗教改革就是把被歪曲的道理扳正,现在我发现宗教改革有更深层次的精神,就是以信为本,而不以理性为本。
圣经是神的话,但是我们凭什么说圣经是神的话?当代有的圣经学者研究很久后得出结论说,这是神的话;但是另一些人也研究很久,却得出结论说圣经不是神的话。所以,我觉得解答这个问题的思路是:我先信圣经就是神的话,然后再慢慢研究它。同样,天主教说圣经是由教会来确认的,教会拥有最终的权威,而加尔文却说虽然教会确认了圣经,但那不过是教会有这个福分,而不是说教会因此就取得了比圣经更高的权威。施洗约翰把基督指出来了,他难道就比基督更大吗?以信为本,真是宗教改革中一个深层次的精神。无论是天主教,还是当代的圣经批判,背后都是以理性为本。“一定要越来越合理”,这真是一个危机。“唯独因信称义”这个道理其实是不合理的,跟人的天然宗教本能完全相反,你分析它的各个层面都是人不能接受的。预定论也是这样的。最初我为什么反对预定论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它“不合理”。
从这个角度,我有时候想宗教改革是“反智”的,同时也与某种奥秘性的体验有关,也就是说:没有一个真正好的圣经的结论,或者是神学结论,会跟圣灵的工作毫无关联。无论是读马丁•路德还是加尔文,我觉得他们好像是某种意义上的神秘主义者,这个“神秘”不是那种“神秘兮兮”,而是他们个人在福音里藉着圣灵有的体验(核心是以救恩为中心的体验)。实际上,他们是在与神打交道时进入到某一个研究中。因此,有时候我会想当代的改革宗和过去的加尔文有什么区别?我觉得区别挺大的。在改教家里面有一种真正的先知精神,他们不像是“文士”。
提出问题4:如何从圣灵在改教家生命中的工作来看他在当代教会中的工作?
约翰——
对于宗教改革,我起先觉得它只是过去的历史,没怎么关心;后来,我意识到神学学习其实是接受某种神学传承,我就问自己:我所接受的传承是什么?在追根溯源的时候,就会首先回到宗教改革时期。我发现自己认为理所当然的某些道理,原来是宗教改革时期再次发现圣经的真理而得到的,其中有关得救的确据、称义和成圣的关系等等,对我的事奉有很大影响。
当我重新认识到马丁•路德个人的信仰体验之后,我对宗教改革神学的理解也活泼起来。我不是仅仅从个人的信仰体验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而是说神在马丁•路德身上的工作,让他能够对神的义有很深刻的体验。我从马丁•路德的体验,又想到自己的体验。如果对文献形成的过程一无所知,神学在文献的层面就可能是死的。这种认识,对我理解宗教改革神学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不再把宗教改革的诸多内容当成是历史,或是某种文献,做一些学术性的讨论,而是把这些内容和自己当下的信仰体验放在一起思考。这时我发现改教家们所谈论的内容与我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对经文所指的实在的一些体验,使我能够更加清楚地明白圣经,实际上这会成为在牧会、讲道中的重要素材和动力。
我们这个时代相对于宗教改革时期,末世的征兆更加明显和浓厚。宗教改革并不是完全的,只有圣经是完全的,但是宗教改革是能够把我们带回到圣经的路。然而,我感受到,中国教会整体而言,对于宗教改革是陌生的。中国教会的基督徒一开始接受的教导,其实就是改教家重新发现圣经而留下来的道理,所以说除非意识到需要重新考虑信仰立场,或是遇到了纷争和冲突,要去确认自己的对错的时候,才会回溯到宗教改革。我也有机会接触到许多老同工,他们能代表近二十年的中国教会历史,而他们那一代对圣经的了解,远远不如受过基要主义神学影响的1949年以前的信徒,就更谈不上神学素养的问题,而且长期以来的反神学倾向使他们不太关注宗教改革的问题。
但是,最近中国教会有一批人是高举改革宗教会和改革宗神学的,因此也推崇宗教改革神学和改教运动。不过,我认为有危机在其中。因为他们相当强调的,实际上是教会建制以及相关当代文化的各种议题,而在我看来这两者恰恰与宗教改革背后的推动力或成因没有任何关系。如果将加尔文教导中由堂会制度引申的教会建制,甚至谈到宪政的问题等,认为是宗教改革的果实,我认为是对宗教改革的曲解,甚至会导致真正的宗教改革遗产更加被埋没。我觉得还是要从马丁•路德个人的生命体验,走进宗教改革的世界。
提出问题5:中国家庭教会如何继承改教传统?宗教改革对于当下中国家庭教会建造的意义是什么?
以宗教改革精神五问今日教会
问题1:我们现在试图淡化宗教改革,趋向与天主教合一吗?其中隐含着怎样的危机?
本刊编辑:我以前听说过,当代教会有淡化宗教改革的倾向,例如一些人想要绕过宗教改革回到教父时期,认为这样才能真正解决我们和天主教的关系问题。
岩铎:我曾经看过一份资料,一次,在一个天主教组织的基督教青年牧师和天主教神甫一同参加的国际活动中,大家一起为教会合一祷告,此时一位基督教的牧师站起来说:“我们跟天主教的主要分歧是什么?使我们必须分开的理由是什么?”在场都是一些受过很好的神学训练的牧师,但大家都沉默,没有谁能很明确地说出来。然后又一位基督教的年轻牧师说:“看来这就是我们的事实,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分离的,却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必须分离。”我相信,如果在中国也举办一个类似的聚会,聚会中有一位风度翩翩、学识出色又表现出很强宗教敬虔的天主教徒问:我们为什么必须分离?我想得出的结论其实是差不多的。大家感受到我们与天主教事实上是分开的,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分开。但是,果真没有理由分开吗?还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失去了使改教家当时不得不分开那个理由?那么我们现在没有的这个理由,就是当时宗教改革的精髓。如果我们没有了,那就是我们失去了这个精髓。
我觉得对于想要回到宗教改革之前的教父时代的人来说,这种考虑与其说是一种基于学理的思考和判断,不如说是基于比较强的体验和某种价值倾向而来的指向——教会合一最大的分歧点不就是更正教和天主教吗?那如果继续再谈那个导致分歧的教义重点,就不仅跟天主教得分,跟亚米念、卫斯理也得分,甚至改革宗内部也得分,所以要想教会真的合一,就要回到宗教改革以前,以没有堕落的天主教和没有分离的更正教统一接受的大公教会传统为基础来合一。但是这个其实分明是天主教的立场。
约翰:“三自”也是这个立场。
本刊编辑:因为“三自”其实也是认同并参与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
约翰:其实合一运动背后有很多理由,其中一个我觉得是基督教本身的生存危机。因为基督教越来越边缘化,所以很多有政治智慧的人,肯定会考虑把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联合在一起,一起做一些事,一起抵制一些事。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这是人很自然的一种倾向,但也说明教会可能会越来越受实用的考量所影响。
本刊编辑:这让我想到约沙法和亚哈谢合伙造船要往他施去(参代下20:35-37),以及与亚哈一起联合抗敌(参代下18:1-19:3)。
瓦器:我觉得提摩太所说的宗教改革的两个外部特征:争辩与分离,是需要作定义的,不然单就争辩与分离的现象而言,会出现很多误解。
岩铎:这里不是这个概念,当然,争辩的现象一直有,而且我们也一直普遍反感它,但关键是整体而言,我们越来越趋向于认为争辩本身就是错的,这是共识。因此,就有了比导致必须争辩和分离的那个理由更重要的价值——就是不争辩不分离。这确实是现在的风气,而宗教改革时期并不是这样。这构成了一个价值公式。
提摩太: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淡化宗教改革呢,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思路找原因:第一个是历史的逻辑的角度,即从教义史的内在逻辑演变过程中找原因;第二个是肉体的原因,在我们之外的福音与我们的肉体的对抗,神的义与人的义的对抗。是不是因为我们不再高举神的义而试图高举人的义,所以淡化宗教改革以及它带来的争论呢?其中隐含的危机,可能是福音会被重新埋没。当我们试图回归宗教改革的时候,是向后看,但是同时要更强烈地意识到我们离主来的日子更近了。回归宗教改革,同时也是在末世的背景下看我们对教会和福音的理解。
问题2:宗教改革的核心精神是什么?当初改教家们关切的核心问题,今日教会还关注吗?
本刊编辑:卡尔·楚曼认为“将那位在基督里彰显自己的神,置于教会生活与思想的中心”是宗教改革的核心精神。这体现在:第一,教会强调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第二,强调圣经是我们宣讲基督时所依据的基础和准则;第三,教会强调得救的确据是所有基督徒的正常经验。大家认同这个定义吗?
约翰:我在想,当时的天主教徒会认为他们并没有把基督当做自己生活和思想的中心吗?
岩铎:而我想问的是,改教之前的天主教会问这个问题——我们是否以基督为中心吗?还是这样问:我们是否顺服大公教会的教导?
约翰:以基督为中心可能是宗教改革之后的一种说法。
瓦器:所以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教会生活与思想的中心到底怎样体现出来”,这也涉及到宗教改革的原则和精髓。
约翰:我觉得宗教改革的核心精神就是五个唯独,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就是以圣经为本。我觉得改教家共同的特征是解释圣经,然后在其中得出结论和答案。这跟当时的天主教学者有明显的差别。
岩铎:我觉得在谈宗教改革的精神、天主教和更正教的区别之前,要思想一个前设,就是当时的天主教和改教家们共同关切什么问题。在至关重要的事情上的分歧才会导致分离。从我一般的了解来说,我认为当时的宗教改革涉及到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得救的问题,这是他们觉得需要拼命,可以为之而死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灵魂永远的去处,关乎救恩。对这个问题的关切使他们感到相关的神学争论是极为严肃而重要的。
第二个是,他们认为教会的教导对于基督徒的生活是支配性的要素,以至于教导的分歧是意义重大的事。
第三个是,教会的体制和基督徒的生活,应当和他们所相信的、足以使他们得救的那个信念相一致。因此,在得救信念上的改革会导致基于这个关切而有的神学体制和信仰生活的改变。
而这些改教家跟当时的天主教共同关切的前设问题,在今天的教会中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搁置一边了。比如说,对得救的关切还是不是今日基督徒生命中的核心关切呢?教会的教导是不是真的如此重要?教会生活和教会体制是和实现足以使我们得救的信心相关,还是和教会生活要达成某种功用的效率相关?我觉得在这三个方面,我们和宗教改革时期的差别特别大。因此,即使我们现在重提改教家区别于当时天主教的命题,其含义都和当时的概念有差异。所以,我们先要考察自己的前设对不对,不能理所当然地跟着时代换了前设。
我注意到的传统中对宗教改革精神的说明有两个原则,一个是形式原则:唯独圣经,一个是实质原则:因信称义。这两个原则在我看来是改教家们的共识,既是马丁•路德的,也是加尔文的,也是慈运理和其他改教家的。当时瑞士的改教家们对因信称义的教义可能没有经过很复杂的争论就直接通过了,所以他们对此的关注也不是很强,他们的热心在于在圣经的教导上建立教会体制和信仰生活,加尔文也是这样。
本刊编辑:宗教改革的时代是一个宗教意识弥漫的时代,很多人关切的是作为一个罪人,自己在面对神的公义审判时,怎样可以不被定罪,已经死去的亲人怎样能够脱离炼狱,进入天堂;而今天这个时代是相当世俗化的,人们对灵魂不关心,对永生不关心,把神排除在自己的考虑之外,因此也缺少因为将要面对神而生出的焦虑。人们现在更关切的是今世的状态:心灵怎样得安慰,困难怎样得解决。所以灵恩派中有一支是非常迎合人的这些关切的,就是成功神学,它将对罪得赦免和永生的关切,偷换成对今世生活如何变得更丰富的关切。
瓦器:在福音的阐述上,原来是得救的问题,今天变成医治的问题;原来是悔改的问题,今天变成更多是辅导和安慰的问题。
约翰:所以在这个处境中谈宗教改革,我就有一种很难受的感觉,中间需要一个转换:宗教改革时期有没有与我们这个时代相似的地方?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卡尔·楚曼提的这点是相当不错的,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彰显自己的神”,而且神是主动彰显,而不是人要求神彰显。我在思想与五个唯独中的“唯独神的荣耀”相对应的是什么?中世纪的教会生活和神学方法所体现的,有没有可能是从人和人的需要开始的呢?刚才提摩太说到“神的义”和“人的义”,中世纪的神学和教会的信仰实践是不是就在这个“人的义”上走岔路了?
瓦器:我也感受到是这样。我们可以从宗教改革精神的对立面作为切入点,来和今天对话。比如“神的义”和“人的义”的分歧,可能在当时天主教里的呈现样式和我们今天不一样,但本质是一样的。
约翰:如果这样考虑,宗教改革家们很多改革的成果真是我们这个时代相当需要的。
本刊编辑:我觉得宗教改革时期所关切的问题,以及改教家基于圣经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今天的教会有非常深刻的意义。在这个世俗化和后现代的世代中,这些能使我们回到改教家所发现的圣经要我们关切的问题上去。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神面前,作为罪人是被定罪的,而且因此要承受死亡,甚至进入到地狱的永刑中。我们是活在神忿怒中的罪人,所以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能源危机,不是气候、转基因或者其他问题,而是罪与死的问题,是我们在神面前怎样不被定罪而被称义、怎样不是进入地狱的永刑而是进入永生的问题。回到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改教家们所珍视并用生命捍卫的因信耶稣基督、藉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复活而使我们罪得赦免、得以称义、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真理,就成为对我们今天同样甘甜而满有能力的应许,也让我们去经历这个应许。总而言之,我们要回到圣经要我们关注的问题上,也从圣经提供的答案里去回答这些问题。
问题3:为什么宗教改革开始的时候,福音的冲击力如此之大,而同样传承下来的教义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却似乎没有那么大的冲击力呢?
瓦器:我觉得现在所注重的神学方法、神学潮流使我们在整体上对宗教改革所关注、强调的方面疏远了。例如现在大家更多关注以圣经神学的方式来解经,相对来说不太强调教义解经,在神学院更推崇释经式讲道,相对来说会忽略主题式讲道。看过去改教家们的讲章,在带出教义和教义的运用力度上是不一样的。
岩铎:我觉得这样区分教义神学和圣经神学在讲道上的应用不太合适。宗教改革就是圣经的发现,以至于在神学方法上摆脱了以前基于哲学框架而有的建立神学架构的努力。当时的宗教改革甚至可以说是试图脱离哲学式、体系化的教义而重新解释圣经的运动。
宗教改革是释经的改革。那么,如果今天的释经有问题,所需要的应该是释经的改革,而不是从释经的神学再转回到别的上面。宗教改革及其后继者实际形成了释经的原理,首先是历史文法解经,但是这是通过圣经本身确认圣经是在讲耶稣基督的事,因此如果某种自以为科学的释经讲的不是耶稣基督的事,它就是违背圣经,因此不被改教家接受。我觉得今天的这些问题与其说是释经带来的,不如说是因为现在释经的原则与改教时期的释经原则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本刊编辑:的确,改教家的讲道是释经式讲道,马丁•路德和加尔文都是做释经的工夫,从中阐明出关于基督的教义,然后关联当下。而当时天主教的释经比较典型的是寓意解经法,天主教也脱离圣经独特的启示根据哲学体系来建立经院式神学的架构。改教家们却承认圣经的明晰性,并且回到圣经里发现福音,发现神话语本身的能力,形成了历史文法的解经,成为在整个释经历史上范式的转变,也是回到安提阿学派的传统。今天我们强调历史文法解经,或者说释经式讲道,跟宗教改革的传承是有关系的。
但是我多少又能理解一点瓦器的观点。今天我们强调的释经式讲道和圣经神学的解经,其中有一些失去了改教家那种基于圣经的对于神学焦点和整个教义体系的关注,因此就变得很琐碎,不能连在一起,也不能突出焦点。马丁•路德通过解经发现“因信称义”,然后他又通过“因信称义”看所有的经文,这个是有统领性的,而且强调整部圣经是显明基督。马丁•路德发现十字架神学,他也用十字架神学贯穿所有的讲章。加尔文也是这样,他基于对圣经的研究,写出了《基督教要义》,然后《基督教要义》的神学架构又帮助他理解每一段经文,所以他甚至认为《基督教要义》写出来是要帮助神学生明白圣经。而我们今天就缺少这个。所以我们的解经就偏离了圣经本身的焦点,和圣经向我们启示的真理的整体性和福音的核心,因此就带来解经上的问题。
瓦器:对于教义的关注和现在的释经,甚至可以说是脱节的。这是教义在今天教会中的冲击力减弱的其中一个原因。释经讲道和对于圣经神学的强调——我不能说所有的圣经神学,圣经神学现在是多元化的,方向、关注点很多,它更能体现出多元化的后现代思想在解经上的影响——与对教义的关注脱节了,这种现象使得我们解经应用的关注和教义的关注不一致。
本刊编辑:也就是说,当我们今天重视教义的时候,有时候只是对教义表述的一种注重,却失去了在教义背后活泼的带着能力的神的圣言,而我们对圣经的关注呢,与圣经所显明的整体教义根基又是脱节的,所以就进退失据,产生种种问题。
瓦器:这也让我想到,虽然马丁•路德跟加尔文其实都比较厌烦和痛恨中世纪以阿奎那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神学进路,而以释经的方式重新建立教义,但后来无论是路德宗还是改革宗,都重新强调以经院化的方式来建立教义系统。这导致对于教义的阐述开始抽象起来,不是那么活泼了。所以,路德宗后来出现了敬虔主义来回应经院主义倾向,而改革宗在清教徒的神学里有比较好的平衡,既有理性强经院化的特征,又有释经的深切应用。今天圣经神学的发展,虽然是受多种思潮影响,但实际上也提供了丰富和强有力的方式,使得我们可以重新回到教义真正关注的部分。问题就在于,我们应当如何使用它所提供的方法,活泼地进入到起初教义所要呈现的应用。这个也许可以使我们回到宗教改革。
问题4:如何从圣灵在改教家生命中的工作来看他在当代教会中的工作?
约翰:当代社会在思想、生活体验等很多方面,是将“神和他的作为”抽离出去的。灵恩运动其实也是自觉和不自觉的针对这个时代所谓的“神不在场”的回应,因为它至少能够让人在体验上意识到“神在场”,而且,神在你生活中最需要的那些部分里,例如生命的丰盛、健康、某种情绪上的调整等等。这个世界,人其实活得相当艰难,越来越不像人,如果能提供一种不同的生活,那会有一大批人跟从。我自己面临个人和教会牧养中的困境时,也自然会想到这些。说句玩笑话,甚至有时候,我会想有没有“改革宗+灵恩派”。
杖恩:之前我也有类似的关切和想法,我曾经关注的加尔文主义循道会,它强调的是教义和体验性的结合。《基督教要义》第三卷的核心问题是关于信仰的本质问题,是从谈圣灵开始的,第二章用了很长的篇幅讲什么是真正的信心,但在那之前第一章先谈圣灵与奥秘联合。我曾试着问为什么不是第二章在前面。所以之前我说为什么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有一种“神秘主义”的倾向。奥秘联合、与基督联合是加尔文的讲法。
岩铎:改革宗的救恩论就是圣灵论,改革宗里面包含着对圣灵工作的经验和相当精确的描述。我以前跟一个灵恩派的牧师说:“灵恩派最大的问题就是不重视圣灵。”他很生气,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为什么说你们不重视呢?因为你们不区分一般的灵性经验和对圣灵的经验,也不试图区分,如果重视和尊重圣灵,就不会容忍这种混淆。”这是因为他们缺乏明确而且严肃的基于圣经的圣灵论。
本刊编辑:就像刚才约翰说的,这个时代也产生了一种对于现代主义的理性化、工具化、物质化的反动,就是人们心里追求超自然的灵的经历。灵恩派也是迎合了这个,不管是说方言也好,先知预言也好,还是经历神迹奇事,它应许你可以有灵的体验。但灵恩派的强调点跟宗教改革关注罪得赦免和永生永死太不同了。显然灵恩派在所关注的问题和给出的答案上都是对宗教改革的一种偏离,都错了。那为什么还要提“改革宗+灵恩派”呢?
瓦器:“改革宗+灵恩派”这个词出来,其实反映了一个常见的现象:改革宗的救恩论确实是圣灵论,因为圣灵使我们与基督联合,但问题是我们知道改革宗的救恩论,可是却缺乏对圣灵工作的强烈体验,我们体验不到圣灵是那么活泼地把救恩成就在我们身上。这时好像改革宗的救恩论和圣灵的工作脱节了。因为缺乏改教传统当中常见的这种教义在经验层面的关联,所以转而拥抱灵恩派,羡慕他们有一种经验的表象。而之所以有这样的原因,就像刚才所说的,是因为在传讲过程中我们不知道救恩、教义是怎样应用在实际的经历当中,以至于我们好像觉察不到圣灵的工作。如果知道教义是怎样活泼地应用在日常生活里,我们感受到的福音震撼力、我们生活的改变、我们对圣灵的体验应该是非常强烈的。
提摩太:站在更高的高度看,我想我们应该知道宗教改革运动是圣灵发动的吧,因为圣灵来是要见证基督,宗教改革时期重新发现了基督,在本质上这是圣灵工作的结果。所以,在这个时代如果我们想更好地继承宗教改革,这样的努力其本质仍然是圣灵在这个时代的工作。
本刊编辑: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今天成为一个依靠圣灵的改革宗时,我们的特点就是持守改革宗对于人完全堕落,以及唯有耶稣基督的替代性救赎能够使我们罪得赦免且有永生的这样的教义。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切切地祷告,祈求那位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也叫人明白福音的圣灵,将人最根本的问题显明在人心里,也将福音显明在人心里,使人知道福音是人的唯一出路。这是依靠圣灵的改革宗所应该有的服事和生活。
问题5:中国家庭教会如何继承改教传统?宗教改革对于当下中国家庭教会建造的意义是什么?
提摩太:其实回想咱们刚才谈过的,大家慢慢形成一个共识是:当说到回归宗教改革,不仅要回归宗教改革的结论,也要回归宗教改革当时所面对和讨论的问题。我想将布鲁斯·L. 雪莱《基督教会史》的一段话读给大家:“新教用新的方式解答的四个问题:一、人如何得救;二、宗教的权威性何在;三、何为教会;四、基督徒生活的真谛是什么。”我非常认同这四个问题应该是宗教改革关注的四个问题,对这四个问题正确的回应,应该是宗教改革对于今天中国家庭教会建造的意义所在。
本刊编辑:这四个问题不仅是宗教改革关注的问题,也是圣经本身、是早期使徒们所关注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不再关注这些问题,其实不只是偏离改教传统,而是说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偏离了圣经和神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
瓦器:我在思考家庭教会的传统是什么。教会历史中所传下来的东西不能都叫传统,传统是指那些显明于圣经当中的真理很活泼地体现在教会里,这是我们要追随的。在一种比较封闭、受苦的环境中,家庭教会自己探索和发展出来的,是一种朴素的、强调经验和祷告的、受苦的、与世界分别的、背十字架的传统。而对于改革宗所保存下来的那种对于教义系统的深入认识和经验,在中国传统家庭教会当中是普遍缺乏的。所以为什么今天的中国教会会出现“改革宗热”,这也体现出以前的路好像走不下去了,然后在改革宗传统中寻求突破。在我接触到的传统家庭教会的老同工里,有一些已经接受了改革宗,他们说刚开始接触改革宗的时候,发现改革宗里对于恩典和律法之间关系的论述,对他们的帮助很大。另外在教会的发展中,他们也体会到改革宗在教义与教会建制这两方面的教导,对于家庭教会非常宝贵。当然有的传统家庭教会也仍然在原来的传统当中排斥改革宗。
岩铎:我觉得今天的“改革宗热”基本上跟改革宗的精髓没多大关系。中国教会接受改革宗是以“理性和经验的力量”为接触点的,而不是以改革宗神学对福音惊世骇俗的说明为动力。改革宗对于中国教会的知识分子意味着一种事在人为的处事态度,讲规则、讲果效,并且用理性和经验衡量事物。
我认为传统是福音带来的生命在具体的处境中展现出的某种理解、行事方式、某种价值,并且它有两个意义上的连贯性:一个是实际意义上的连贯性,另外一个是神学逻辑上的连贯性。它是一个群体在一段时间里共有的,有着时间和神学逻辑的连贯性,并且展现出具体的形态、神学理解、价值……我觉得中国家庭教会传统是在1949年以前就有了,其特征主要是教会处于被主流社会排挤的情况下形成的特别形态——注重灵魂得救,个人的悔改重生,圣灵的能力,走与世界分别的十字架道路,整体而言表现出比较强的和直接的末世论倾向,但是相对来说也表现为不太重视对教义比较具体和系统的分辨,并且反体制。
但是,我认为中国家庭教会在不是很有神学自觉的情况下形成的传统,其中有一些东西是挺宝贵的,和宗教改革的精神非常吻合(我认为也是在圣灵的恩典下形成的)。然而,不自觉的情况下形成的特征,一旦使它形成特征的环境稍稍变化时,它也会变化。我觉得中国家庭教会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到1980年,第二个阶段是1980年到1990年,第三个阶段是1990年以后到现在。
1980年以前,家庭教会完全是地下教会。1980年后则是在相对开放的情况下,形成了某些家庭教会的不够成熟的体制、神学上的自觉,但却是脱离了大公教会传统连续性的自觉,和出于需要而有的临时性的建制的努力。1990年之后,大量知识分子进来,家庭教会开始自觉地确认身份,在这个确认中有两个方向:一个是跟大公教会的传统接轨,另一个是确认自己社会性的身份。这两个方向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这身份是被基督救赎了的群体,而这个救赎不是1980年以后在中国开始的,而是早在亚当就开始了,从五旬节教会成立一直梳理下来,所以也是宗教改革的后裔;另一个是一种有形的情况下的身份自觉,从这个方向上所谈的大公教会传统,也是从一个社会集团的角度去理解——是源远流长的,有比较强的社团历史。所以在1990年后慢慢形成的城市新兴教会,或者说独立的、开放的、新兴的中国家庭教会运动,我认为是跟中国家庭教会的传统反对的,甚至身份意识上也不愿意说自己的源头是中国家庭教会的传统,那它是从什么意义上来说自己是延续宗教改革的传统呢?
提摩太:因此就同时偏离了两个传统。
瓦器:我觉得甚至会以宗教改革传统来否定家庭教会传统。
岩铎: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宗教改革对中国家庭教会的价值在于:带来基于福音的再发现而获得的真正的大公教会传统意义上的神学自觉、事工自觉、体制性的自觉等等。除了反体制以外,我认为中国家庭教会传统是跟宗教改革的精神非常一致的,但是它缺乏自觉,而这个自觉,或者是在知识分子主导的社会性身份自觉的情况下发生,或者是在连于福音再发现中建立。
本刊编辑:也就是说,您认为中国家庭教会的传统跟宗教改革的精神在许多方面是有很强的一致性,但问题是这些一致的方面是不自觉地形成的,因此就面临两个问题:第一,它怎么传承?第二,它在环境改变的情况下是否还能持守?所以今天如果中国家庭教会能够连于宗教改革的传统,特别是宗教改革福音再发现的传统,那就会帮助中国家庭教会建立基于改教精神的神学上的自觉、牧养上的自觉、体制上的自觉。以福音为核心的信仰告白和神学信念,将在各种处境中胜过环境影响而成为可传承的。在牧养方面,改教传统可以给我们很多牧养的经验和资源,使我们知道怎样将这样的神学信念落实在弟兄姐妹的生命中。体制方面的建造又保证这样的牧养的进行。这将是宗教改革对于建造中国家庭教会的极大的帮助。
 《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
《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