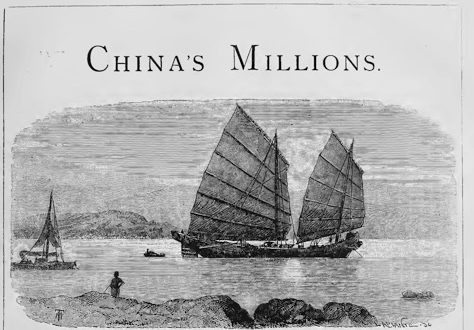编译/亦文
引言
1860年,戴德生带着妻儿回到英国养病,被医生警告,以他们的身体状况,若再返回中国,无异于自杀。戴德生身在英国心在汉,始终关注中国禾场的种种动态,眼看在华宣教士因为各种原因病退、早逝、辞职、转业、返乡,人数不增反减,他心急如焚,奔走各大差会,呼吁他们增援中国禾场。但不同差会的回应,几乎如出一辙:没有更多的人力可派。其实,这些现有差会的赴华前辈们,也曾做过类似的呼吁,但收效甚微。其中原因众多,除了众教会未能兴起回应,加上亚非拉其他禾场的分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传统差会对“宣教士资格”过于狭窄的界定:男性,神学院毕业,具备按牧资格,可以执行施洗和派发圣餐的圣礼。因为大部分赴华差会在英美两国成立,这一信息也很难传到其他欧洲教会。[1]观察到这种种局限,戴德生成立内地会前后,便开始招募平信徒到中国去,也接纳姐妹们加入宣教团队,后来更是为小语种宣教士入华服事建立了合作平台,快速并大量地扩大了宣教士的队伍。本文将着重回顾后两种“宣教储军”于庚子教难后,在山西子禾场的服事。
妇女事工
庚子教难的惨剧无形中挑战了内地会宣教策略中一个重要的尝试:招募并差派单身女宣教士进入中国尚未对外开放的腹地。
早在1878年,也是在山西,也是因为灾荒,亟需女宣教士前往灾区投入妇孺事工。[2]当时,内地会同工需要照顾的孤儿已达两百名。团队中的女性同工都是新人,无法独当一面,戴德生想来想去,只有自己的太太可以胜任。戴德生的续弦福珍妮(Jane Elizabeth Faulding)在1866年加入内地会兰茂密尔团队(The Lammermuir Party)时,还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姐妹。她到达中国之后便崭露头角,在杭州与中国传道人王来全合作无间,成立了自负盈亏的男校和女校,并积累了内地旅行和生活各方面的丰富经验。1878年,福珍妮嫁给戴德生已有七年,两人的孩子一个两岁,一个三岁,还有玛莉亚所生的四个孩子需要她抚养。因为中国的宣教事工,戴德生常常奔走各地,两人聚少离多,当戴德生向妻子提出这个不情之请之际,夫妇俩刚在分别一年多后团聚了四个月。为此祷告了两周之后,珍妮清楚地知道神的意思是要她去。当戴德生的妹妹贺美(Amelia)听到嫂子要一个人返回禾场,便决定免除她的后顾之忧:“如果珍妮蒙召回中国,我便蒙召照顾她的孩子们。”当时,也有教会的老姐妹不认同“抛夫弃子”的作法,珍妮在亲情、传统和马其顿呼声的张力中,再次如基甸般向神求印证,神也再度在一周内回应了她的祈求。
1878年10月,在鲍康宁(Frederick Baller)的护送下,福珍妮和两名新同工:何丽(Celia Horne)与柯丽梅(Anna Crickmay),抵达太原。丁戊奇荒下的山西是全中国唯一默许“洋鬼子”赈济灾民、怜恤妇孺的地区,出现了空前宽容的福音机会。福珍妮在很短的时间内,和英国浸信会的李提摩太(Richard Timothy)及循道公会的李修善(David Hill)设立了手工艺技校(industrial school),供妇女靠手艺谋生。一度有1156名孤儿和孤老在诸差会的救济扶助之下。1879年2月,珍妮完成了她的任务,把工艺技校和孤儿院转交给了何、柯两位姑娘,回到上海和刚从英国返华的戴德生团聚。[3]
因此可以说,内地会在山西的事工,从一开始就和女宣教士们的冒险、投入、牺牲分不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神保守了深入内地的外籍女同工的安全,祝福了她们的服事,内地会的“巾帼策略”得到了母会和母国的默许。但是,庚子教难期间,被义和团拳民直接杀害,以及在逃难途中病弱而死的宣教士中,很多都是单身女子。人们难免再次质疑,让弱女子们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深入腹地,拓荒植堂,是否是明智之举?1903—1905年之际,数位驻晋女宣教士的书信和报告,从不同的角度回答了这些问题。虽然各地宣教报告多少都会提及妇女事工,以及女性同工的重要性,但大多比较零星简约,而出自女宣教士笔下的报告,则提供了较为详尽生动的细节。
服事霍州教会的“三合一”女教师
冯贵珠劫后重返
在日内瓦长大,精通英法等语言的冯贵珠(Evangeline F. French)早在1893年便加入内地会,来到中国山西,与来自新西兰的苏梅兰(Edith E Searell)姑娘相交甚厚。庚子教难初发,贵珠写信到孝义(Hiao-i)问比她大十岁的苏姑娘当何去何从。苏姑娘在6月28日那天回信给她说:
你信中谈到,这地方很有可能比那地方安全一点。但是,亲爱的贵珠,从人的角度来看,我想通通都是不安全的;可是,生命若是藏在基督里,那里就是安全的。主的儿女有处避难所,那是至高的隐密处。上主是我坚固的保障,无论现在或是永恒,在祂里面有平安。我们是否只因为减少了一点我们所希望的寿数,就口出怨言呢?“在地上少了一刻时光,在天上便多一刻时光”,“生命越是短促,就越早接近永生!”
这封信成为苏姑娘的绝笔。信寄出两天后,她便与同工魏美例(Emily Whitchurch)一起被暴徒打死在孝义的礼拜堂,临死时四手相持,一如她们生前祷告的样式。当地传道人冒死为她们收尸,暂时停放在新建成的洗礼池中。
怀揣苏姑娘遗书的冯贵珠,和其他宣教同工结队南下,历经千难万险,九死一生逃到湖北汉口,路上曾绝望地看着陆义全夫妇(Albert A. & Elizabeth Lutley)一岁半的幼女在自己怀中断气。因担心车夫嫌尸体不吉利而赶人下车,全车人只能强忍悲痛,默默地轮流抱着逐渐僵硬的弱小尸体。[4]而欧亚大陆的另一头,冯家的老母和幼妹贵石(Francesca French)日夜悬心,最终盼来“平安抵鄂”的电报。多年后,在一本自传体著述《主所做成》(Something Happened暂译)[5]中,如此描述劫后重生的冯贵珠:
默默回归家族圈的,是一个大为消沉的冯贵珠。因漫长的身心折磨而产生的冲击,完全压倒了她。展望未来宣教生涯时,没有任何足以使她振作或憧憬之处。她大部分的朋友都遭残杀,她自己也降到严酷现实的谷底。当人不断不体谅地问她所有述职宣教士都会面对的问题:“你难道不渴望回去服事吗?”她报以沉默,因为她无法诚实地说“是”,而回答“不”,又会留下错误的印象。
在中国禾场,无论摆在她面前的是何等责任,对她而言都是责无旁贷、无情无悔的,但是无法不惧怕自己将为之摆上什么。她的身体渴望休息,她的精神状态需要一定的消遣,但是在属灵层面,她尚未能从各种聚会和证道中得享受,获益处。她饱尝如此深刻强烈的属灵经历,如今只求通过静默和独处来测度其长阔高深。最具疗养果效的时段,乃是她在挪威度过的一个较长的假期,在一个峡湾中的美丽岛屿任意徜徉,远离述职宣教士所需应对的种种压力。当时机临到,她已完全做好返回禾场的准备,但是现在她仍锱铢必较地计算代价,明知在她面前最难之事尚不是个人受苦,而是在至亲之人身上所施的进一步的痛苦。
分别自是伤感,所有亲友都知道她此去之后怕是难以再见慈母一面,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接受这一事实:妹妹贵石将面对极其孤独的一生,难以满足她本性中各样合理的渴望。尽管母亲深感失去爱女之痛,贵珠仍毫不犹豫、毫无疑问地同意返回禾场,因她深知对中国信徒的亏欠,而其中一些人曾冒着生命危险搭救了她。贵珠走后,冯母的体力每况愈下,很快便行在死荫幽谷的初道阴影之下,那是必死之人预备灵魂穿戴不死之冠冕的地方。[6]
1902年11月13日,初返山西的冯贵珠在信中提到[7],在太原逗留的五天中见到很多老朋友。信徒童老爷(T’ong Lao-ie)的女儿媤姑娘(Si Ku-niang)告诉冯姑娘,那位1900年在介休(Kiai-hsui)保护过宣教士们的陈老爷(Ch’en Lao-ie),是她父亲的好友。他们一起求学,又都是浙江同乡。有一阵子,陈老爷在太原府候选就职[8],就在那时,他的孩子病了。叶守真太太(Mrs. Edwards)[9]悉心医治陈家的孩子,症状渐退。无人知道那件善行在多大程度上促使他后来保护逃难的洋人。冯姑娘继而写道:
我看到了因殉道者而立的各种纪念碑,还有他们的墓园,但是这些都似贫乏无意义。但是当我站在府台衙门前,即他们被杀之地,却感受到难以言传的庄严。他们的呼求:“……要等到几时呢?”[10] 即便在为他们而立的纪念碑都风化之后,仍然为神垂听。我们也去到了他们生前最后两天住的房子,大屠杀时看门人也在场,他向我们描述当时的场景,比我们之前听到的都更绘声绘色。当下的百姓们都非常害怕,没有人敢承认自己曾是大屠杀的目击证人。我也很有兴趣地和一名男信徒聊天,他其实看到米姑娘(Miss Rice)和胡姑娘(Miss Huston)[11]受攻击,及米姑娘被杀,只是他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神在那些日子如何试炼那些信徒,着实还有不少故事。
冯贵珠到了徐沟(Hsu-keo)[12]之后,每天都召集住在北城的九名信主的小媳妇和大姑娘们聚会,也帮助戒烟所的五名妇女戒除鸦片。她们大都聪明好学,愿意听福音,进步稳健,令人欣慰。在平遥(P’ing-yao)大会上,有六名从徐沟去的人受洗,其中四人是妇女。她们每天都喜乐地来报到,早上是年轻人,下午则全体到齐,听从冯姑娘的教导,并希望有一位女宣教士能久住此地。
安顿不到一个月,冯姑娘又赶去参加12月10–11日在孔庄(K’ong-chuang)举行的联合聚会。在短短几天内,她便发现这里的妇女极其真诚,对救恩之道非常清楚,也渴慕受教。其中好几人是原先在霍州(Hoh-chau)和洪洞(Hong-tong)的教会学校受教的。那些没有受过当有教导的妇女,错不在她们。其中大部分人记得古姑娘(E. G. Gauntlett)在1900年的造访。所有受洗的妇女都不缠足,虽然其中一些人是不久前才放了脚的。[13]
盖群英毅然来华
没过多久,冯姑娘便迎来了一位新同工,盖群英(Mildred Cable)。早在1893年,盖姑娘就在一次宣教聚会上,听过魏美例姑娘的分享,与她有过短暂交通。当她接受完培训,准备前往中国之际,庚子教案爆发了,而神使用来呼召群英前往中国的魏姑娘则是在义和团手下最早遇害的一位。在一个紫丁香盛开的5月上午,盖姑娘收到了原本准备一起赴华的未婚夫的分手信,这根“最后的稻草”,几乎把这位敏感自敛的弱女子压垮。然而,盖群英仍然坐上了1901年秋的远洋轮船前往中国。[14]到了山西之后,贵珠带着群英悼念了魏、苏两位女宣教士殉道之地孝义,再回到同样有两位单身女宣教士殉道[15]的霍州(Ho-chau)同心服事,展开了未来数十年的亲密同工。《主所做成》一书如此描述这两位亦师亦友的女宣教士在这段重建时期的心路历程[16]:
摆在她们面前的是一个庞大的任务。在义和团运动这一可怕浩劫的冲击下,教会几近瘫痪。虽然有些人因着这一经历而更坚强茁壮,其他人则似乎难以恢复原状。宣教士们必须走访每一个村庄,探访每一户信徒家,长时间地聆听各种令人心碎的故事之后,才有可能开口略做一些鼓励、建议或劝勉。这正是冯贵珠的长处。而对于盖群英而言,作为一名默坐聆听的新人学到经验,乃是最好的培训。
两年后,冯姑娘记录了当地在庚子教难之后第一次像样的聚会:18人受洗(十女八男)。十名妇女中的六人曾在冬季农闲期间和女宣教士们一起学习教义,另两人是女校的学生。另一人是77岁的老妇人,多年前就已信主,但一直没有机会受洗。有一位从本城铜关(Tong-kuan)来的老人和他的太太也被接受了。老夫妻最初是去年信主的,在初冬便销毁了家里的偶像。这些都是一位梁太太(Mrs. Liang)所结的果子。她虽未受聘于差会,却像一名女传道(Bible woman)一样服事,热心地传扬救恩之道,当圣灵在人心动工之后,又耐心地教导他们。 [17]
盖群英笔下的“山西霍州的学校事工”[18]
在冯贵珠的带领下,盖群英很快全身心地投入服事,在霍州创办了一所女校。她的文字恩赐,也逐渐受到《亿万华民》编辑的赏识,长篇地刊登她的详细报道:
我曾在近期的日记中试着描述造访乡间的一天。但要对本宣教站的一天作类似的描述则更为困难。目前有70名媳妇和姑娘和我们在一起,有些住在戒烟所之内,其他人则是来参加为期18天的圣经班。在学校的庭院里有36名在读女童,她们都是信徒的女儿;加上8名年轻媳妇在此受训。
女校基本达到自给自足(self-supporting)。女童们带来足够自己和老师们吃的面粉做口粮,差会只需负责教师的束修。小媳妇们当然也完全费用自理,戒烟的瘾君子们付费入住!(作为席胜魔牧师创建的天召局之一,没有外人会认为我们靠戒烟发财!)
我们对那些进城来受教的妇女免费供应食宿,缘由众多。主因是当我们下乡时,不论逗留多久,她们都视我们为客,总是用最好的东西招待我们,不期待任何回报。因此我们一有机会就款待她们也是理所当然。各地区的执事将有心参加培训之人的名字交给我们,但我们只邀请那些日后足以辅导别人的可塑之才来就读。
但是,我想要特别描写的,乃是我们自己的学校。去年开学时,只有25名学生,校舍虽然进出方便,但并不宽敞。今年年初,母国的一位朋友汇来一笔钱,让我们用在当地建筑所需。她并不知道我们的需要,因此我们视之为神的供应,便在女校建了一处新庭院。1904年11月1日,这座庭院建成开放,陆义全监督和几位家长在此聚集,祷告赞美神。
如果我的读者借着想象与我一起来到霍州的话,我们将穿过校舍,结识住在其中的一些人。首先,我们会走进一个四方形的大院子,树木扶疏,三面建有房间。朝南的房间住着年轻的媳妇们,她们大多嫁给了投入福音事工的男信徒,我们的目的之一便是训练她们成为可以肩负职分之才。她们都是热心的信徒,渴慕学习更多的圣经知识。
每天的课程包括:新旧约的学习;在我们的督导下,到学校各班和戒烟所作教导;掌握对戒烟病患和妇孺最有益的方法;认读罗马拼音化的中文,坚持读圣经,并标出不认识的汉字和费解难懂的段落。她们每周有一小时可以就此发问,而我负责答疑,有时候那些问题真的很为难人!我们和她们一起学习“大卫的一生”,“希伯来书”,“会幕”和“基督的一生”。
每天早上9点之前,是她们祷告和读经的时候。
庭院这一边的下一个房间乃是教室,四壁以地图为饰(当然是本地所制),还有贾上校好心寄给我们的一副史姑娘(Miss Stevens)和贾姑娘(Miss Clarke)的照片。照片上的横幅写着“直到祂来”[19]四个汉字,两边的对联则是启示录2:10[20]。我和冯姑娘便是在这间教室传授所有课程,通常安炕(砖床)的地方放了桌椅。这间屋子外面,还有一个小间,常常会看到教师们在那里利用静修的时段乐读圣经。
接着进到一间做卧室的大房间。庭院的西边是一间学生屋(schoolroom),也很大,坐满了九到十六岁的孩子们。墙上是一张课时表,标明除了一小段自由活动外,孩子们会从清晨5:30忙到傍晚7:30。
当然,圣经是最重要的功课。她们要记诵很多经文;先背诵马可福音,然后背诵圣经中不同的章节。大部分岁数小的孩子们都能正确地讲述和解释耶稣诸多的比喻和神迹。她们也开始学习书写难学的汉字。我们现在开始使用王杭通(Wang-Hang-Tong音译)编写的入门教材,效果良好。
短短数月的在校操练,在女孩子们身上带出的改变是惊人的。她们中大部分人的家庭,对她们不是呵斥,便是宠溺,顺服和纪律对她们而言是新鲜事。今年我们欢喜地看到六个女孩受洗。
读到这里你们是否愿意为我们而祷告?使我们谨守在祂里面到一个地步,我们的生命得以彰显祂的圣名,并教导身边的人更好地认识主。每日身边被这么多人环绕,观察我们的生活,实乃极大的责任。哦,但愿我们永不让人错识那一位,因祂曾说:“当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时,外邦当知道我是神。”[21]
数年后,冯贵珠的妹妹贵石,也前来中国。霍州的信徒亲切地称她们为“我们的三合一女教师”(our three-in-one teachers),英文文献里则称她们为“三人行”(The Trio)。[22] 后来这三位女宣教士,在年过半百之际,再起雄心,离开服事多年的霍州,一路西行到河西走廊,五度穿越戈壁荒滩,在西域众少数民族中继续从事福音拓荒工作。
服事大宁教会的众巾帼
古姑娘大宁来信
无论在内地会,还是其他差会的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三人组合。譬如,在庚子教难期间,三位在大宁(Ta-ning)殉道的女宣教士,便是一对姐妹(聂凤英和小聂姑娘/Frances E. Nathan & May R. Nathan)加上一位单身女同工(郗秀贞姑娘/Eliza M Heaysman)。教难之后,其他女宣教士也陆续返回当地。1902年12月,古姑娘从大宁写信说[23]:当地和四乡的信徒非常热情地接待了她。老牧师激动地说不出话来。虽然物是人非,责任巨大,故地故人仍让古姑娘十分喜乐。有些信徒保持了鲜活的信心,有些跌倒的信徒已经悔改,急于重新开始。神也打开很多新的事工之门,各村都有人丢弃家中的偶像,还有其他人表示也准备这样做。
古姑娘说的老牧师,很有可能是驻堂牧师张知本(Chang Chi-pen)。他原是大宁城外一家庙宇的主持(head Buddhist priest),因在1881年得到一本马可福音,为求真意,赶回12英里外的家乡北桑峨村,请教一位叫渠万镒(Chü)的年轻塾师。两人研读之后,心门渐开,先以熟习的偶像崇拜方式对这本福音书,以及耶稣和十二门徒焚香礼拜。不久他们又获得一本新约全书,为之欣喜若狂,对真理的认识更上层楼。废除偶像之后,张先生又拂逆地方官的意思,辞去方丈一职。这位官长下令严刑责打他,以至于昏死过去。渠先生也被传去,因不愿再参与文庙的礼拜仪式,两度当众受杖,夺去举人功名,以示羞辱。几年后,他们听说平阳府住着一位洋教士,便马上赶了三天路程,前去府城拜会德雷克教士(Mr. Drake)[24],并在那里发现,几位老乡也已信了耶稣。短住数日之后,两人返乡,比以往更热心地与人分享救主,甚至翻山越岭跑到五日脚程之外的孝义,告诉原先学佛的同修(co-religionists)。他们第一次走访孝义,便有八个家庭毁掉偶像,转向真神,其中三人后来成为这一带的教会执事。1885年,张、渠两人受洗归主。先后有两百多人加入了大宁的教会,年长的张先生成为驻堂牧师,达十年之久,深受爱戴。年轻的渠先生也成为这一带的巡视牧者(general pastor),他凡事感恩赞美主,令宣教士们联想起英国的救世军(Salvation Army),他在讲道方面也颇有恩赐,主领聚会大受欢迎。[25]
在大宁与张、渠两位中国传道人合作的众巾帼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来自挪威的麦瑞章姑娘(Miss K. Rasmussen)。1879年,英国奋兴家雷金纳德·拉德克里夫(Reginald Radcliffe)[26]唤起了挪威人对海外宣教的热忱。挪威南端克里斯蒂安桑(Kristiansand)的一名成功商人,拉斯马森(Rasmussen)和他的家庭,开始密切关注中国内地会的事工。四年后,范岚生牧师(Rev. Frederik Franson)[27]来到拉斯马森家主领聚会。范牧师是一位瑞典裔美国福音派布道家,对宣教动员颇有负担。听到他的分享后,先是拉斯马森家的家庭教师Sophie Reuter和女仆Anna Jakobsen(喻姑娘)受感蒙召前往中国,前者嫁给了剑桥七杰之一的司米德(Stanley Smith),后者成为湖南境内的拓荒者。她们的中国来信,进一步燃起了家乡人的宣教热心。庚子教难前夕(1899年),拉斯马森自己的宝贝女儿Karrilla也来到了中国,取名麦瑞章,年23岁;三年后(1902年),庚子教难硝烟初散,拉斯马森家族另一个女子Cessi也来到了中国,取名麦英华,年32岁。
1903年6月19日,麦瑞章姑娘完成本季最后一次下乡探访,为期一周,回到大宁后在信中写道,义和团闹事期间,渠牧师在一个叫Shang-ü的村里住了一段时间。当地村民之前曾听过福音,但从那时起才开始认真地慕道。麦姑娘一行约在周六傍晚开饭前抵达该村,有些妇女从未见过洋人,却仍格外地热情款待,准备了乡间最好的食物。一有机会,她们就坐到炕上,渴望学习读经。有一名妇女的丈夫希望她放脚,她也很乐意听从。另一名妇女说:“你们下次来的时候,我们就都变大脚啦。”几个到了缠足年龄的小女孩,仍保持着天足。有六个家庭丢弃了偶像,其中几家想请人去教导他们,不少年轻人在渴慕更多地认识真道。但要做的事太多了。[28]
谁能想到,第二年夏天,这位渴望为神、为中国人做更多事的麦姑娘,竟染病去世了。1904年1月的《亿万华民》上刊登了一位署名E.M.S.的女宣教士的回忆[29]:
我第一次见到麦姑娘,是1899年,在培兰路(Pyrland Road)的准宣教士培训之家。我和麦姑娘一见如故,那时还不知道,不久后我们会坐同一条船去中国。到了中国之后,我们在扬州的女宣教士之家度过的时光是何等快乐啊,每个人都迫切憧憬着自己未来的事工。麦姑娘始终心系山西,因几年前从她家乡出去的宣教士时不时地传回山西禾场的消息。我们都很爱她,她的年轻、聪颖,有目共睹,她喜乐的灵和热切的使命感,是我们众人的榜样。经过几个月的学习,我们分散了,她得到了“心里所求的”[30],北上入晋,而我则加入了江西贵溪(Kwei-k’i)的那个小团队。我们几乎没有想过,要过多久,又将在怎样不同的情形下才能重逢。
1900年在汉口,我们看到了受尽义和团的折磨,又藉着神的恩典被奇妙地拯救出来的一些朋友。一天早餐时分,另一群病弱不堪的同工逃到汉口,麦姑娘就在其中。他们也经历了神相助逃难的奇迹。故友重逢,我们格外感恩,祂让我们得以再聚首,是何等的恩典。
当我们中间的一些人可以返回宣教站,而女宣教士们仍不能返回山西时,麦姑娘加入了我们在贵溪的工作。最初几个月,她在城里和我们住在一起,接着又搬到罗姑娘(Miss Elofson)[31]主持的一个福音支站。她是多么爱农村的百姓啊,对她而言,和当地的女信徒结伴下乡传福音,是何等乐事!但是她的心仍在山西。1902年秋,她离开我们返回那里了。若神的旨意许可,我们何等希望她能留下来一起同工。她走了之后我们又是何等怀念她。
大宁成了她的宣教站。“这是一个快乐的地方,”她写道,“感谢神让我回到山西,是祂把这样的感动放在我的心上。主把我差派到这里实在是好。大宁拥有自己优秀的本地同工,每个周日,福音会在整个地区14个地方被传讲。四五十个村子里都有基督徒和慕道友,还有很多人丢弃了(put away)偶像。信徒们对我们太好了。”她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所署日期为1904年6月10日,其中讲到平阳府的一个大型聚会,大部分山西同工都参加了,也就是史洛恩先生(Mr. Sloan)[32]参加的那个聚会。“我们度过了快乐有益的时光,”她加上这一句,接着继续讲述她们的工作——关于渠牧师:“他的事工由神做主,”又提到一位新执事分别为圣出来事奉,以及建设可以坐得下五百人的新礼拜堂,如何给学童们上课并教导圣经,还有很多待走访的乡村 ——“当神赐力量的时候,便诸事亨通。”
这个夏天,她和其他人一起从大宁到K’eh-cheng避暑,小住几周。到了7月末,她感染了伤寒,且是致命之症。病来如山倒,短短几天内她便安息主怀。在病倒的日子里,她得到了盖群英姑娘、冯贵珠姑娘和古姑娘的悉心照顾。盖姑娘如此写道:“能做的,我们都做了。在那个偏远的小村子里,主奇妙地供应了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回头来看,我着实因此感谢神。我们失去了一位亲爱的朋友,中国失去了一位忠心的工人,因她对妇女得救的热心着实令人难忘。”她的监督陆义全先生写道:“我们的姐妹是一位被珍视的工人,她美好的品行,已经赢得了大宁中国信徒和教牧领袖的信任与爱戴。”
祸不单行,年仅28岁的麦姑娘过世前后,张牧师和渠牧师这对“同修变同工”的本地领袖也相继去世。大宁教会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失去了三位属灵领袖,只剩下古姑娘一人勉力维持。
小结
除了大宁,其他地方的女宣教士们也在竭力服事当地教会,并见证到多年耕耘所带来的果效。1903年7月30日,和思义姑娘(Miss J. F. Hoskyn)在信中说:平阳女校原来的姑娘们,带给宣教士们很多喜乐。那最早入学的五六个年长的女孩子们谦逊勤勉(modest and industrious);而已经嫁为人妇的姑娘们,成为丈夫们的良配,受到婆家的赞誉。[33]
同年12月21日,介休(Kiai-Hsiu)的莫姑娘(F. L. Morris)也在信中提到:五里外的某个村庄里,有三个家庭渴慕真道,想更多地认识基督。妇女们捣毁了家中的偶像,男丁们定期参加聚会。其中一人的妻子来到介休宣教站,一方面接受风湿症的治疗,一方面领受信仰的教导。她是聪慧之人,已经背下了很多经文,数首诗歌,跟着女宣教士们识字,也学得很快。此外,城里还有一两位已经转向了基督。[34]
二十世纪初,三晋大地上散居着无数位像冯氏姐妹、拉斯马森家族众女子、盖群英、古姑娘、和姑娘和莫姑娘这样默默耕耘的女宣教士。她们飘洋过海、翻山越岭,将青春岁月、锦绣年华献给了这片贫瘠的土地,即便性命受威胁,也在所不惜。她们中很多人终身未婚,仿佛嫁给了山西,也有不少人殷勤服事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埋骨于山西。
伙伴差会[35]
为了尽早把福音传遍神州大地,戴德生不仅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招募单身姐妹为宣教先锋,还跨越语言文化的障碍,欢迎其他欧洲教会的合作和加盟。内地会成立后第一批赴华同工中,就有一位瑞士籍的女宣教士夏安心(Louise Desgraz),在福珍妮之前救护山西孤儿的正是她。
19世纪80年代初,一位瑞典的年轻人在伦敦与戴德生几度邂逅,并到内地会的办公室深谈,等他在1883年10月返回瑞典时,已是内地会的忠实朋友。这位叫霍姆格伦(Holmgren)的年轻人,不仅是某基督教周刊的编辑,也是斯德哥尔摩(Stockholm)某大教会的牧师。他把从戴德生口中听到的中国属灵需求传递给了瑞典教会,其中一名叫埃里克·福尔克(Erik Folke)[36]的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校友深受感动。与此同时,范岚生牧师因听到戴德生的呼吁,产生了促进欧洲各国成立差会的异象,他的奔走呼吁,促成了欧陆和北欧六个差传机构的成立,瑞华盟会(Swedish Mission in China)便是其中之一。[37]1887年,福尔克以瑞华盟会首位宣教士的身份前往中国,和其他内地会的男教士一起,在安庆培训学校学习语言,起名符励恺教士,算是内地会第一位正式的伙伴同工(Associate Member)。第二年符教士北上赴晋,于11月由运城北门进城。看到符教士在中国内地安定下来后,瑞华盟会邀请戴德生到瑞典首都带领聚会。此时,戴德生和内地会的故事,因着霍姆格伦的文章和讲章已经在瑞典广为人知。1889年11月1日,戴德生和次子戴存义医生(Dr. Howard Taylor)抵达哥德堡(Gothenburg),同一天便向两万人分享宣教信息,接下来的一个月内,几乎每天都会向两到五千人证道。年近花甲的戴德生虽然体力渐衰,却仍坚持坐三等舱,自己提行李,令同行人印象深刻。到了斯德哥尔摩,三天中既有三千五百人的大型聚集,也有与瑞典索菲亚女王(Queen Sophia)及宫廷女官的私下读经。在一条条讨论解释内地会的管理章程“原则和实践”(Principle and Practice)之后,瑞华盟会的领袖决定整体加入内地会作为伙伴差会(Associate Mission)。在接下来的五年中,有百名瑞典男女青年递交申请,其中21人通过筛选前往中国。
19世纪80年代中期,范岚生牧师从北欧前往欧陆大地,发现在德国巴门(Barmen)的信徒已经在为中国禾场发热心了,范牧师“火上浇油”的信息,促成了德华盟会(Deutsche-China-Allianz Mission)的成立。内地会愿意协助新兴差会前往中国的消息传开后,促使新差会的领袖纷纷写信给内地会的伦敦办公室,询问是否能按瑞典、挪威差会的先例那样,成为内地会的伙伴差会。范牧师和他的瑞典裔传道同工鄂教士(Emmanuel Olsson)于1890年6月2日,与内地会的伦敦咨委会面谈细则,成立了瑞典圣洁会(Swedish Holiness Union)。同年12月3日,鄂教士带着两名新同工,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以归化城为中心,向长城内外的百姓传福音。[38]
1890年,戴德生在上海举行的第二次赴华宣教士大会上,呼吁众差会在五年招募一千名新人献身于中国禾场。同年秋,范牧师回到美国,在纽约的布鲁克林(Brooklyn)带领布道学短期班,首期五十名学员中,有二十人回应了中国禾场的需要。紧接着,他又在芝加哥、明尼阿波利斯、奥马哈等地推广同样的短期课程,至翌年1月中下旬,已有35人通过宣教士甄选,扬帆远航;2月初,又有15人紧随其后。这便是北美瑞挪会(Scandinavian Alliance Mission)的滥觞,亦即日后更名为协同会(TEAM/The Evangelical Alliance Mission)正式成立前的赴华差传部。范牧师还协助宣信牧师(A. B. Simpson)成立差传机构,招募到六十多名新人前往中国,在晋北长城内外拓荒,即日后闻名遐迩的宣道会。[39]那时候,离庚子教难的爆发,只有短短数年时间,而这些西方青年在那个历史转折点奔赴中国,不是病逝,便是遇害,鲜有存活。
这些非英语系教会成立赴华差会,由内地会协助抵达中国后,在神州各地建立了一个个小范围的子禾场。伙伴差会的宣教同工除了额外的英语培训外,和内地会的同工接受同样的中文培训,在禾场享受一样的待遇,使用外汇转款、宣教站点等同样的“基础建设”。伙伴差会的监督同时也是内地会中国咨委会(China Council)的成员,共商大业。主要的区别在于他们隶属的差会(sending society)各有不同。
在当时山西的宣教禾场中,瑞典圣洁会的宣教士在晋北服事,瑞华盟会的宣教士在晋南开拓。和内地会本身的英语同工所负责的片区一样,瑞典同工牧养的众教会也都在慢慢恢复,商议建堂事宜。下面是这些北欧同工的报告,由于母语非英语,他们的报告相对比较简洁。
晋北:瑞典圣洁会
1890年成立的瑞典圣洁会,在山西左云(Tso-Yüin)、朔平(Soh-P’ing)、应州(Ing-Cheo)、浑源(Hun-Yüan)一带服事。1900年6月29日,圣洁会的十位同工,在朔平城外全体殉道,尸首被挂在城门示众。这十人乃是内地会体系最早殉道的一批同工,享年都在三十上下。[40]整个差会只有当时返欧述职的高教士(Augutus Karlson)幸免于难。半年后(1901年1月),第一批来到伦敦内地会女子准宣教士培训所的,便是来自瑞典的同工。经过一段时间的语言学习之后,她们于同年9月扬帆前往中国,“取代她们殉道的姐妹们”。[41] 硕果仅存的高教士也回到了左云,1903年时,他身边已有三位年轻新同工,事工再次展开。他们以左云为中心重新走访各城,受到百姓欢迎,丰镇(Feng-chen)和大同(Ta-tong)也有了负责同工。[42]
1904年7月28日,高教士在左云记述了众多“献给神的果实”[43]。主奇妙地祝福了浑源州的福音支站Chuang-O。高教士在那里和贾尔麟(Oscar Carlén)、贺赖德(J. D. Höglander)[44]两位弟兄一起同工,为时一周,每天都有聚会,最早一场始于上午7点,最晚一场从晚上8点开始。神的灵大大彰显。不少男女老少请求祷告,当着会众的面在主前认罪。共有25座偶像被带到福音站。其中一个非常庞大,一路拖到这里,已磕碰得七零八碎。村民们交出五座黄铜铸成的偶像给宣教同工,作为这不寻常的一天的纪念品。
7月17日下午所举行的那场聚会奇妙难忘。成群的人们聚集在狭窄山谷的树荫下,听高教士传讲永生真道,然后看他走进水中,为18人施洗 (5名男子和13名妇女),接纳他们入会。这些人慕道都颇有时日。
村民们还请高教士选定建造礼拜堂的地方,在长老、教师、信徒和非信徒的陪同下,高教士查看了被提议的堂址,以及奉主名分别为圣出来的田地。
晋南:瑞华盟会
晋南一带,瑞华盟会的成员也全力展开了他们的事工。符励恺教士虽然身体欠佳,仍返回禾场,他从运城(Yun-ch’eng)发出的信中说[45]:事工全面发展。在解州(Wai-chau)地区,孔先生(Mr. K’ong)的呼吁激励人心,当地信徒开始努力,把福音传给同胞。在春季的大集市上,狄教士(Mr. Tjader)如常搭起他的帐篷。为兴旺福音,当地信徒踊跃地出钱出力。
胡林德教士(Mr. L. Hugo E. Linder)[46]在猗氏(I-shï),也忙得不可开交,极其需要女宣教同工。在过去一年,裴庄(Pei-chuang)的教会产生了真正的传福音心志。好些男女信徒在周日到邻村和集市上作见证。其中一村的五六个家庭因而成为真信徒,周日来参加崇拜的人数成倍增长。裴庄的信徒负责承办该村的聚会。在圣诞节的早晨,他们先在裴庄举行了清晨礼拜,再到礼拜堂分享爱筵,共有八十名男女参加。当旧礼拜堂显得太小时,他们向差会借了钱,买下一处新的堂址。别人享乐偷闲的新年期间,他们却忙着收拾聚会场所。已有约两百日的劳作用在新址四壁的修建上。裴庄和孙庄(Suen-chuang)的教会即将在新礼拜堂聚集,准备迎见范岚生牧师。孙庄的教会已经抵押贷款,购置了与裴庄新堂相仿的场地。差会以租用的方式资助他们建堂,也便于在走访期间在那里落脚和聚会。临晋(Linchin)的教会租用了一个场地,其他两处的教会也在打听建堂的事。宣教士们尝试推广自给自足的原则时,便发现当地信徒已醒悟过来,看到自己作为神的子民,当尽什么本分。[47]
译者感言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其他禾场,历史上的女宣教士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首先在人数上,自从“差传编制”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向姐妹开放以来,宣教团队的性别比例就长年保持在1(男性宣教士):1(宣教士妻子):1(单身女宣教士)的黄金比例。若在宣教团队中删去单身女性这个群体,海外禾场势必会流失三分之一的人手,众多宣教站无法开拓或维持。如表一显示:1905年之际,内地会体系中的女性宣教同工占61%;单身女性同工(包括未婚和丧偶者)占35%。
表一:内地会体系宣教同工男女人数和宣教站人数(1905年)[48]
| 男性 | 未婚
女宣教士 |
师母 | 丧偶的
师母 |
总人数 | 宣教站总数 | |
| 内地会 | 262 | 215 | 177 | 18 | 672 | 154 |
| 伙伴差会 | 63 | 55 | 33 | 2 | 153 | 45 |
| 总数 | 325 | 270 | 210 | 20 | 825 | 199 |
| 比例 | 39.4% | 32.7% | 25.5% | 2.4% |
表二进一步显示:内地会体系下199个宣教站中,单身女宣教士驻守其中33个,换言之,有16.6%的宣教站没有男性宣教士主持;驻守这些宣教站的105名单身女宣教士,占宣教士总人数的12.7%。[49] 众多省份中,单身女宣教士独当一面的现象在江西禾场尤为突出,实因戴德生在19世纪80年代策略性地在广信河流域建立一连串以女宣教士为主的宣教站。[50]本文所提到的麦、施、罗三位姑娘曾服事过的贵溪,便属于“广信河女子宣教区”。而另外还有很多宣教站,都是一对宣教士夫妇和多名单身女同工组成的团队。
表二:内地会体系中仅有女宣教士所驻守的宣教站(1905年)
| 省份 | 宣教站地名及女宣教士人数 | 总人数 |
| 甘肃 | 镇远(3) | 3人 |
| 陕西 | 西乡(2)、洋县(2)、郿县(2)、引家卫(2)、桑家庄(1)、武功(2)、汧阳(2) | 13人 |
| 山西 | 介休(2)、霍州(3)、大宁(3)、蒲州(2)、潞城(2)、曲沃(3) | 15人 |
| 山东 | 宁海(2) | 2人 |
| 河南 | 西华(2)、扶沟(2)、永宁(2)、陈州(2) | 8人 |
| 江苏 | 清江浦(2)、安东(4) | 6人 |
| 四川 | 新店子(3)、南部(2)、营山(2)、广元(2)、巴州(3)、夔州府(3) | 15人 |
| 江西 | 安仁(4)、东乡(2)、贵溪(5)、上清(2)、戈阳(4)、河口(3)、广信(2)、洋口(3)、玉山(4)、永新(3) | 32人 |
| 安徽 | 池州(2) | 2人 |
| 浙江 | 路桥(1)、缙云(2)、云和(2)、兰溪(2)、常山(2) | 9人 |
| 合计 | 33个宣教站 | 105人 |
其次,从功能而言,女宣教士更容易进入家庭,接触妇孺,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在男女授受不亲的远东和中东,若没有女性同工,宣教士们便无法接触一半以上的人口,福音也难以在家庭生活中扎根和传承。女宣教士管理创办的女校,师生若是同吃同住,24小时无死角地“零距离接触”,则极大限度地达到言传身教的果效。难怪盖群英校长要请英国教会为神在她身上“道成肉身显为圣”而恒切代祷。
西方女宣教士们不仅挑战自己,突破传统,背井离乡,不让须眉,也把同样的信念传递给了禾场的女信徒们。“三合一”的女教士们坚信,姐妹和弟兄一样,应该在真道上受造就,教会有责任给予妇女“当有的教导”,建立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庭生活,女信徒在品行和知识上都应该在同村妇女面前有好的见证。正是在这样的信念下,三人认真系统地教导大姑娘和小媳妇,所传授的课程内容包括新旧约,甚至包括相当冷门的“会幕”知识。当“顺服与纪律”取代了“呵斥或宠溺”,女校信徒们身上的变化是惊人的。霍州的女子有福了,这或许是数千年来,这一带的乡间妇女第一次得到受教育的机会。
今天说起内地会的宣教士,通常想到的都是英联邦和北美的成员,很少会留心来自北欧和欧陆等国宣教士的奉献和牺牲。由于缺乏介绍,文献又以小语种为主,大部分学者望而却步,亟需有心人慢慢考察,让内地会系伙伴差会的事工也逐步进入读者的视野。回到十九世纪,一方面,当时非英语的小教会要投入中国这个巨大庞杂的禾场,障碍重重;另一方面,像内地会这样没有宗派背景的差会吸纳非英语的同工,也是顾虑多多。戴德生最初对内地会的定位是英国差会,因此即便是同样说英语的北美教会要加入进来,也是慎之又慎,唯恐打破团队的同质性。但是深思熟虑之后,他借用不同宗派差会“睦谊协约”(comity agreement)的禾场传统,以“小分队、子禾场”的方式勾划出众伙伴差会平行并进、遍地开花的运作蓝图,让每一个小差传团队都有自己可以耕耘的“一亩三分地”。这种合作方式弹性很大,既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内地会(如夏安心、麦氏家族的四位女性)或借调给内地会(如符教士),也可以以整个差会加入内地会的大家庭(如瑞华盟会),开辟众多禾场的大差会也可以把赴华同工这支小分队托付给内地会(如协同会和宣道会)。于是,在山西一省,在内地会的体系下,我们便看到宣道会、瑞典圣洁会、瑞华盟会和内地会本身四大团队的并肩努力。如表一显示,1905年戴德生去世之际,内地会本身有672名同工,而内地会系的众伙伴差会加起来共有153名宣教士。因着与小语种教会分享在华宣教的基础建设,内地会为亿万华民多招募了相当于自身团队22.8%的福音勇士。
因庚子教难期间,几乎所有同工皆殉道[51],宣道会将山西绥归道的事工转给内地会,到广西、甘肃、湖南、安徽等地重起炉灶,继续谱写如火如荼的宣教篇章。与此相仿,瑞典圣洁会亏损到只剩高教士一人,但他仍愿带领新同工返回左云,这种前仆后继的精神,都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当年戴德生的尝试,对今天华人教会参与宣教,也提供了另一种模式。虽然北欧背景的差会,与英语系的内地会存在语言不通、文化有异的障碍,却在宣教大业上仍同心合作。伙伴差会的准宣教士,要先学英语和英美宣教士沟通,再学中文和方言向中国当地人传福音,但他们不因困难多而却步,或因人数少而气馁。
女性同工和伙伴差会,笔者在把这两个貌似完全不相干的话题整理成一篇文章的过程中受到提醒:这两股力量在宣教史上,曾经是被忽略的零散兵力,却在十九世纪末,被戴德生这位差传领袖打破传统差传思维,有创意、有智慧地揉合进了宣教大军中,大大推进了神州大地的福音事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神可以通过我们向万族万民做什么新事呢?语言、方法和文化,不仅是前方宣教中需要跨越的障碍,也是后方差派时需要突破的盲点。
[1] 早期赴华宣教士中也有极少数非英语系的西方宣教士,如瑞士巴色会(Basel Mission),荷兰宣教会(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的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等等。
[2] 中国华北地区发生于1875年(丁丑年)至1878年(戊寅年)之间的一场罕见的特大旱灾饥荒。史称“丁戊奇荒”。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称之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波及山西、直隶、陕西、河南、山东等省,造成一千余万人饿死,另有两千余万灾民逃荒到外地。
[3] 详参:The Shaping of Modern China: Hudson Taylor’s Life and Legacy, Volume 2 (1868–1990), Piquant Ltd., 2005, 330-35;董艳云(Phyllis Thompson),《内地六巾帼》(薪尽火传——福珍妮篇),林嘉亮译(香港:海外基督使团,2007)。
[4] 黄锡培编著,《回首百年殉道血——一九〇〇年义和团事件殉道宣教士的生命故事》(美国中信与海外基督使团联合出版,2010),458;向素珍,<一本跨越三个世纪的圣经>, 2021年9月23日存取,https://www.xuehua.us/a/5eb599ff86ec4d6195aa8f9e?lang=zh-cn。
[5] Mildred Cable and Francesca French, Something Happened(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Ltd., 1933),100–02. 这本书由冯贵珠的妹妹冯贵石和同工盖群英合著而成,讲述三人得救、蒙召、宣教的生命故事。
[6] 原文取意于哥林多前书15:53-54:“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原文作“穿”)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
[7] “Editorial Notes,” China’s Millions, March 1903, 40–41.
[8] 候选文官和候补文官是指有官职而无实缺的在册官员,这是清朝独具的官场现象,在清朝中期,已十分普遍,晚清时期尤为严重。
[9] 叶守真医生(E Henry Edwards, 1855–1945),1884年3月抵达太原,创建赐大夫纪年医院(Schofield Memorial Hospital),1896年从内地会改入寿阳宣教会(Shouyang Mission),庚子教难期间,返英述职的叶医生是寿阳宣教会唯一的幸存者,翌年返华,与内地会及其他差会一起与中国官员协商善后事宜,并代表寿阳宣教会放弃一切赔偿。
[10] 原文仅有“How long”两个单词,当为引用启示录6:10的表述法:“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
[11] 米姑娘(Hattie Jane Rice)与胡姑娘(Mary Elizabeth Huston)都来自美国,一起在山西潞城(Lu-cheng)服事。1900年7月初,潞城发生暴乱,两人和顾纯修教士全家一起逃亡,7月13日途经山西泽州(Tsehchow,今晋城)时,受到暴徒袭击,米姑娘当场去世,年41岁。胡姑娘受伤倒地后,暴徒用车从她身上辗过,后于8月11日在湖北云梦(Yunmeng)不治离世,年34岁。
[12] 旧县名,今清徐县徐沟镇。
[13] “Welcome News from Shan-si,”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Apr 1903, 54.
[14] Something Happened, 65–77.
[15] 庚子教难爆发时,在霍州服事的两位英国女宣教士史姑娘(Janet Stevens)和贾姑娘(Mildred Eleanor Clarke)转往首府太原避祸。1900年7月9日,山西巡抚毓贤将所有当地宣教士押到衙门前,全部斩首示众。遇难时,史姑娘享年43岁,贾姑娘享年32岁。
[16] Something Happened, 105-06.
[17] “A Bible-woman’s work, Extracts from Letters,”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Oct 1904, 141.
[18] Miss A. Mildred Cable, “School Work at Huochow, Shan-si,”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Apr 1905, 47.
[19] 取意自哥林多前书11:26。
[20] 很有可能是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为底本的对仗句。
[21] 取意自以西结书36:23。
[22] Something Happened, 113.
[23] “From Shan-si,”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y 1903, 66. 古姑娘后来成为戴存信夫人。
[24] 可能是S. B. Drake,1878年加入内地会,1883年退休。
[25] 张、渠二人的见证,《亿万华民》的宣教士报道中多次提到,此处主要参考:Lutley, “The Province of Shan-si,” 84; “Editorial Notes – Pastor Chü of Ta-ning,”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y 1905,61;刘安荣,〈近代山西教徒入教原因探析〉,《宗教学研究》,2005年第3期,175–78;黄锡培,《回首百年殉道血》,“山西内地会华人传道人名单”,473。
[26] Reginald Radcliffe(1828–1899),英国布道家,曾对1859年苏格兰大复兴产生深远影响。
[27] 范牧师(1852–1908),以福音布道及宣教动员著称。
[28] “Extracts from letter,”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Nov 1903, 154. 这里所说的“季”(season),不一定是通常意义上的季度,而是按照当地戒烟所的运作,一季有可能是七到九个月,错开最热的夏季。
[29] “In Memoriam: Miss K. Rasmussen,”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November 1904, 156. 作者当为施姑娘(E. M. Smith)。
[30] 诗篇37:4:“又要以耶和华为乐,祂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31] 罗姑娘全名I. F. Elofson,1891年加入内地会。
[32] 史洛恩(Walter B. Sloan)是英国内地会办事处的总干事,他在1904年四五月间走访了山西各地的教会,平阳府大型聚会的日期是4月28日至5月2日,主题是教会治理和纪律。
[33] “Extracts from Letters,”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Dec 1903, 170.
[34] “Kiai-Hsiu,”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y 1904, 61.
[35] 伙伴差会的加入过程,详参:The Shaping of Modern China: Hudson Taylor’s Life and Legacy, 534–36。
[36] 即符励恺教士(1862–1939)。
[37] 其他五个差会为:丹麦宣教盟会(Danish Mission Confederation),瑞士盟会(Swiss Alliance Mission),德国盟会(German Alliance Mission),芬兰盟会(Finnish Alliance Mission),以及瑞日福音盟会(Swedish Evangelical Mission in Japan)。 所有六个差会至今皆在。
[38] 鄂教士于1894年1月19日,因感冒转肺炎突然离世。
[39] 该差会初名国际宣道联会(International Alliance Mission,1881),主要负责海外需求,后来宣信博士于1897年将其与负责国内需求的基督徒联合会(The Christian Alliance)合并为宣道会(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40] 殉道者分别为:嘉利孙牧师(Nathanael Carleson)、甘公义牧师(Gustaf Edv. Karlberg)、勅生牧师(Oscar A. L. Larsson)、毕德生牧师(Ernst Pettersson)、栢瑾光牧师(Sven A. Persson)、栢师母毕月英女士(Mrs. Persson, nee Emma Petterson)、恩姑娘(Justina Engvall)、隆雅贞姑娘(Mina Hedlund)、祝汉生姑娘(Anna Johansson)、冷姑娘(Jenny Lundell)。
[41] Mildred Cable and Francesca French, A Woman Who Laughed(London: OMF, 1934), 203.
[42] “Province of Shan-si,” Jul & Aug 1903, 99.
[43] 原文:“Fruit unto God,”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Nov. 1904, 157。乃《亿万华民》的主编按照高教士的报告浓缩成文。
[44] 贺教士于1902年来华,驻山西左云。
[45] “Province of Shan-si,” China’s Millions, Jul & Aug 1903, 99;“Editorial Notes,” China’s Millions, Oct 1903, 142.
[46] 胡教士(1868 -?)1893年抵华,驻山西同洲。
[47] “Editorial Notes,” Oct 1903, 142; “Extracts from Letters – Self-support,”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Aug 1904, 106-07.
[48]文献:China Inland Mission–List of Missionaries and Their Stations, Shanghai, July 1905, 36。
[49] 段落及表格中的数据皆以该文献原始数据为基础:China Inland Mission – List of Missionaries and Their Stations, , 36。
[50] 详参:Valerie Griffiths, Not Less than Everything: The Courageous Women who Carried the Christian Gospel to China (Chapter 4: The Guangxin River Women),(Monarch Books, 2004), 97–134。
[51]庚子教难期间,隶属于宣道会的21名宣教士和他们的14名子女殉道,还有10位宣教士和6名儿童向北逃命,穿越戈壁沙漠,到达西伯利亚,再返回瑞典。详参:Little Paul,<在山西阳高殉道的宣道会宣教士>,/archives/gzjn_xdh01.html。
1,584 次浏览
 《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
《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