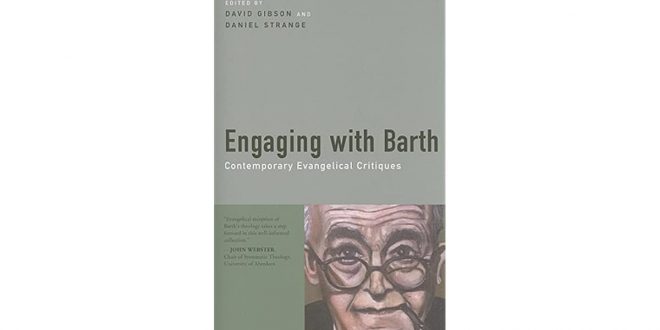文/麦克·霍顿(Michael S. Horton) 译/庆君 校/土明
在小说《整月都是礼拜天》(A Month of Sundays)中,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的主人公是一位长老会牧师,他从同为牧师的父亲那里继承了对卡尔·巴特的喜爱。厄普代克将教堂里沉重木制家具——讲坛、圣餐桌、洗礼盘和会众长椅——的暗指与主人公父亲嗓音的音质编织在一起,他自己的宗教观点表现得相当清晰。这位小说家可能无法全盘接受老普林斯顿(Old Princeton)的正统神学(见他的《圣洁百合》[In the Beauty of the Lilies]),但他也厌恶自由主义贫瘠的、情感泛滥的以及不诚实的做法。“把散落一地的宗教拖干净!”他说,“让我们把真理装在石罐中,或者干脆什么都不要。”
我理解厄普代克脑海里回荡的声音。我在保守的福音派中被养育,并且在许多方面仍然对其感激不尽,然而我还是变得不满足于虔敬主义(pietism):无论其风格还是实质。在相当多的方面,巴特的声音都不同于此:远非情感泛滥,却总是充满恩典。我与巴特之间存在很多分歧,然而他的声音仍旧具有诱惑力,至少部分是由于他的起始点是上帝,那位将所有人都置于祂评价之下的伟大上帝。当福音派被文化束缚以至于教会受到威胁,甚至无法成为这一真理的见证时,唯有巴特的著作继续深入人心才合乎情理。他著名的“不”和“是”打断了福音派与其他主人秘密立约的幕后会议。强调上帝的至高主权和恩典当然从来都不受欢迎,但打垮“天上执政的和掌权的”,正是教会的使命所要求的。然而与此同时,巴特从根本上挑战并重述了改革宗至关重要的教义。在概述这些差异之前,我们先来讨论福音派对巴特的态度。
福音派对巴特的态度
保守福音派和改革宗最初对巴特的态度有所不同。哥尼流·范泰尔(Cornelius Van Til)于1962年发表的《基督教和巴特主义》(Christianity and Barthianism)深刻影响了美国福音派对巴特的广泛评估[2]。然而,这篇文章同时也包含严重的缺陷。遗憾的是,范泰尔那些正当合理的洞察——尤其是巴特拒绝从“之前”(before)和“之后”(after)的角度思考上帝使人与祂和好的行动而带来的影响——有时似乎被过分地泛化和甚至被对巴特自述立场的曲解所掩盖。尽管范泰尔频繁引用柏寇伟(G. C. Berkouwer)对巴特的批评,但这位阿姆斯特丹的神学家与范泰尔较早的分析有所不同,并且在《卡尔·巴特神学中恩典的得胜》一书中给出了他自己更有雅量和更为谨慎的批评[3]。
美国福音派从来没有就应当拥抱还是抵制巴特达成共识。其中一些人或许跟随了范泰尔的批评(却没有同时接受范泰尔更细致入微的评论,尤其是在那本书的开头部分),他们认为巴特比更正教自由主义者好不了多少。查尔斯·雷历(Charles C. Ryrie)称巴特主义是一场“神学骗局”,是披着正统术语外衣的自由主义[4]。
当然,巴特自己充分地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他仍然是“十九世纪之子”,而且最近的巴特诠释者(尤其是布鲁斯·麦考马克[Bruce McCormack]和约翰·韦伯斯特[John Webster])完成了极为出色的工作,他们将巴特置于他自身的历史背景中,认识他所反对的神学同时对他所造成的影响[5]。然而,一个人若熟悉巴特的原著,就会对将他仅视为另一个“自由派”的尝试提出挑战。巴特反对将福音同化到现代思想的范畴,坚定捍卫关于上帝、人的罪、基督的位格和工作的教义,以及在拣选、赎罪、称义、成圣和使罪人最终得荣耀的行动中三一上帝神恩独作的教义。这些内容从他的《罗马书讲义》第二版到未完成的《教会教义学》的最后一个片段,始终主宰着巴特的视野。他比今天很多声称属于宗教改革传统的人更加看重普世信条和改教遗产。[6]与绝大多数自由派和福音派的潮流相比,他引发的革命即使对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批评他的教义系统的教会也有帮助。约翰·韦伯斯特正确地指出了巴特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了神学的整体面貌”,至少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众多学派是如此:“神学家们不再关注普遍的理性、道德或经验,而是与这位困扰于那迫切的呼召,即用人类语言传递上帝的启示话语(Deus dixit)的传道人一起,被牢牢地置于教会之中。”[7]
然而,巴特不仅改变了新更正教主义(neo-Protestantism)的神学图景;他在对教会信仰和实践至关重要的内容上,也彻底修改了福音派和改革宗所秉持的教义。例如,鉴于他对拣选、圣经和洗礼教义的根本性修订,人们只能对伯纳德·兰姆(Bernard Ramm)的声称感到讶异,他说:“巴特的神学是在启蒙运动余波中对改革宗神学的重述,而不是对启蒙运动的屈服。”[8]詹姆斯·达恩(James Daane)、保罗·朱伊特(Paul Jewett)和唐纳德·布洛希(Donald Bloesch)试图将巴特与最好的保守福音主义融合在一起,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的确,若不是从二十世纪下半叶至今被英美福音派(Anglo-American evangelicalism)挪用,巴特的遗产是否还会接近其目前的影响力很值得怀疑。但愿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足够的历史距离,可以认真并且批判性地倾听这位革命性思想家的声音,而不是将他简单地英雄化或者妖魔化。
评估巴特的神学修订
当代很多流行风潮将神学修订或革新本身作为目的,但巴特与许多神学家不同的是,他对此并不感兴趣。他的神学修订总是围绕着这样一个中心:即三位一体的上帝并不因我们而成为上帝,却选择成为我们的并与我们同在的上帝。然而,我将简要分析巴特神学体系中的一些领域,这些领域需要从认信改革宗和福音派的立场对其进行持续批判。除非考察他的基本预设,否则我们不可能评价巴特神学遗产的优势或缺陷。我将从这些预设开始,并试图说明这些预设如何反映在他的实质性结论中。
巴特的本体论
几乎毫无争议的是,在巴特的革命事业中,故事的主要反派是“本体类比”(analogia entis)。除了耶稣基督之外,神与人之间的任何相交都被严格排除在外。巴特认为,将上帝的启示与受造性的历史和自然相提并论,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中世纪教会、新更正教主义和“德意志基督徒”(German Christian)运动诞生的“福音教会”(Evangelical Church)的异教化。作为回应,巴特用粗黑的线条强调了克尔凯郭尔的“上帝与人之间无限的、质的区别”。尽管改革宗和路德宗正统同样强调这种区别(在二十世纪保守派圈子中,没有人比范泰尔更加坚决),然而巴特的结论更为激进。他的本体论影响其教义的全部内容(locus),这可以通过论及两个关键主题来简要概括。
首先,是永恒和时间的脱节(diastasis)。在我看来,当巴特频繁论到“所谓的历史”(Historie)仅仅是“天上的转向”(Geschichte,或如他所说的Urgeschichte)的永恒(原初)历史所投下的“阴影”时,他不仅是创造性地使用柏拉图主义/康德主义(Kantian),而且也似乎仍然在其影响的束缚中。正如布鲁斯·麦考马克所指出的,巴特著名的切线类比(analogy of the tangent)“意味着新的世界仅在一个点上与旧的世界相交,却没有沿着历史的时间线继续延伸。”[9]“巴特试图通过这种‘真实的历史’和‘所谓的历史’的辩证关联达成的目的是相当明显的,”麦考马克补充说,“他想把上帝在历史中的运动(movement)和作为(action)置于历史调查(historical investigation)的范围之外。”[10]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提醒自己巴特那个时代的另一种神学方案,即高等批判对“历史上的耶稣”的寻找,最终否认了使徒所传讲、信条中所宣告的基督,转而支持一些与过去细微的历史联系。到巴特的导师威廉·赫尔曼(Wilhelm Herrmann)的时候,这条线索已经被简化至仅有耶稣的“位格性”。难怪巴特会如此强烈地反对将基督的位格同化到在不信的预设上“重构”的历史中。
因此,巴特采用了克尔凯郭尔以及他在其中受训的新康德主义(neo-Kantianism),试图超越康德的神学遗产。[11]在我看来,这种努力的结果成败参半。尽管克尔凯郭尔强调末世论的重要性(作为他强调上帝的行动超越人类经验、理性、道德和不断发展的宗教意识的必然推论),但他的“永恒时刻(eternal moment)”在没有时间延展的单点事件中穿透历史的概念,无法提供足够的资源将末世论与历史联系起来。我认为,新约的范畴,不是“所谓的历史”(时间–线性)和“真实的历史”(永恒–垂直),反而是“现今的世界”(罪和死亡之下的现实)与“将来的世界”(在公义和生命下的同一现实)。总的说来,巴特采用了现代性的许多预设,这最终导致他在对其进行反驳时不太成功。同康德和莱辛(Lessing),更不用说马尔堡那些更激进的新康德主义者(卡尔纳普[Carnap]和纳托普[Natorp])一道,巴特似乎含蓄地接受了事实与价值、现象(phenomena)与本体(noumena)、理性与信仰、历史与启示的二元论。
由于这个本体论前提,巴特只能将亚当视为基督的影子(shadow),而将创造的历史和救赎的历史视为一对矛盾的术语。受造物不仅与造物主相区分,前者的本体论地位甚至令人怀疑。实际上存在着一种“人类仅仅因其是受造物而受到的咒诅”[12]。事实上,巴特抱怨说,改革宗正统强调永恒的拣选通过时间内的多个阶段并且在历史中的圣约里实现,这是改革宗传统发展中“一个致命的历史时刻”,为将启示(即基督)同化为自由派的历史主义铺平了道路。[13]毫无疑问,他是作为教义神学家而不是历史神学家来诠释改革宗传统中圣约神学的发展。例如,他认为科切乌斯(Cocceius)“因将时间性的救赎历史(history of salvation)的概念引入神学而获得了可疑的荣誉”[14]。对巴特来说,永恒与历史、上帝与人、恩典与自然,是决然分开的。
麦考马克指出,巴特经常使用两种类型的辩证法:一种是克尔凯郭尔式的,相互对立的双方处于无法解决的张力中;另一种是黑格尔式的,在其中两者中的一方在更高的综合(synthesis)中被同化为另一方[15]。事实上,麦考马克观察到巴特的“亚当与基督”的辩证关系是黑格尔式的。[16]我们将在后面讨论巴特的神学修订时看到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辩证思维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汉斯·乌尔斯·冯·巴尔塔萨(Hans Urs von Balthasar)称巴特借鉴了理念论(Idealist)的概念,很明显持有“一种动态的、实动主义(actualist)的‘上帝即宇宙论’(theopanism),即开始和结束(创造论和末世论)的一元论”[17]。“巴特的太多东西给人的印象是,在他关于事件和历史的神学中,真正发生过的事并不多,因为一切都已经在永恒中发生过了。”[18]这种辩证的结果是,无论是自然还是历史,它们的历史性与现实性都变得可疑。只有上帝和祂的行动被赋予了这种不受约束的本体论分量。
因此,毫不奇怪,巴特因其薄弱的创造论(尤其是人论)而受到来自不同背景的神学家的广泛挑战。或许正是这种辩证导致巴特对创造和堕落的描述落入了传奇(saga)的范畴。无论如何,他对与十字架和复活有关的任何“之前”和“之后”的概念都持谨慎态度:历史被如此彻底地同化成了永恒。对巴特而言,启示发生于不在时间内延展的“永恒时刻”,在这永恒时刻中,“上帝同时将启示给予了祂的圣经见证人,以及接受他们见证的人”[19]。这是克尔凯郭尔“同时性”(contemporaneity)的概念,巴特从《罗马书释义》的第一版开始就一贯秉持这个观念。
无论巴特对现代批判的评价如何,重要的是福音派人士要认识到,他是出于这种本体论的考虑,而不是对自由主义神学或批判方法本身的任何依恋,才不愿意将上帝和上帝的自我启示,与历史和历史的(在线性时间内以事件延伸的方式)连续展开相提并论。事实上,巴特的这些举动往往是对他所理解的新更正教主义预设的强烈回应:尤其是各种对“历史上的耶稣”的寻求,它们不可避免地否定了信条所宣告的基督。
其次,巴特的本体论建立在对上帝–世界关系的实动主义(actualist)论述之上。巴特提出了一个激进的上帝的“存有在行动中”(being-in-act)的概念,仅就间接相遇而言承认启示与和解(它们是同一件事)。上帝和启示(就其首要的对象性来说,仅仅就是耶稣基督)从不与自然和历史相交,但此类事件会掠过受造现实并留下影响——就如炸弹爆炸后留下弹坑。因此,启示(从来都只是基督自己)永远不能直接与任何受造物等同。它自始至终是一个行动、一个事件,在其中永恒打断历史,却不能直接在其中被辨别。我认为,巴特思想中“批判性”(critical)的一面强调人类思想和语言无法与上帝的存有和行动相对应,从而导致了多义性(equivocity),而“唯实论”(realist)的一面则强调上帝在恩典中的能力,这种能力在话语事件和现实之间构建了单义性(univocal)的等同。巴特相当具有现代特征的认识论(知识作为对客体的掌握和控制)既推动了多义性的人类行动,又推动了单义性的上帝行动,因此他才甚至可以说,在不可思议的启示事件中,我们“掌握”了上帝[20]。
巴特的实动主义强调削弱了除基督之外,在创造主和受造物之间提供媒介(mediation)的各种尝试。因此在我看来,当巴特在抵制新黑格尔主义(neo-Hegelian)将造物主与受造物、将基督及祂的工作与教会及其工作综合起来时,他的表现是最好的。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似乎从一元论反弹回到了二元论的怀抱,这种二元论不允许将启示直接等同于任何受造现实。
我们再一次看见,这里缺少的要素是类比(analogy)。“类比”表明上帝与受造秩序之间存在着持续的关系,而不是从上而来的突然入侵。而其结果是,巴特的关键主张,即在自我启示中上帝同时是完全显明和完全隐藏的,必须被修改为:上帝是部分隐藏和部分显明的,无论是在普遍启示还是特殊启示中。拒绝类比的教义的结果似乎是一种实动主义的本体论,它同时倾向于单义性(“完全显明”)和多义性(“完全隐藏”)。一种理性主义(单义)到非理性主义(多义)的辩证似乎是他的实动本体论的认识论推论。
正如乔治·亨辛格(George Hunsinger)所强调的那样,巴特的实动主义与他对上帝主权和恩典的核心强调密不可分。[21]因此,他可以同时肯定康德的认识论批判和马尔堡的新康德主义者,而又不会陷入到后者的怀疑主义中,因为上帝已经显明了自己——不仅超越而且对抗了所有的人类能力或者无能。甚至信心对巴特来说都不是核心性的,不像在虔敬主义和自由主义中那样。相反,上帝的和解行动才是焦点,信心和顺服都不过是其结果而不是原因。巴尔塔萨指出:
与加尔文相似而与路德不同的是,巴特不太在意信心的性情(disposition),而专注于所信的内容。事实上,巴特说得很好,他严格坚持神学客观主义(“信心源于其对象”),并且如此彻底地转离施莱尔马赫的自由主义更正教。这是为什么他如此值得阅读,也是为什么我们不必害怕从他那里找到多愁善感的敬虔或空洞的教牧性教诲。所信的内容自己进行教诲,建造它自己的大厦。[22]
很多当代的神学反思,更不用说讲道,很难得到类似的评价——无论是在福音派还是在主流教会。然而,在巴特那里产生的最具有深刻洞见的主题,同时也引起最为严厉的批评。
认识论:巴特的启示神学
强调时间与永恒,或物质与灵性的辩证,而不是罪与恩典,或罪恶之下的“现今的世界”与公义和生命之下的“将来的世界”的辩证的神学,很难肯定那“全然他者”(Wholly Other)如何被在身体和时间内的受造物真正地认识和经验。有限性很容易与固有的缺陷性相混淆;自然本身,而不是罪对自然的败坏,可能被视为受造物与上帝关系的主要障碍。巴特的启示神学虽然对神秘主义,尤其是对任何试图攀登天堂之梯以拥有上帝的人类尝试提出尖锐的批评,但在某些方面,它仍然源自能够在柏拉图主义传统(无论是否是基督教柏拉图主义)中发现的时间与永恒、物质和灵性的对立。一种以“极端超越性”(hyper-transcendence)为基础的激进怀疑(多义性),不过是另一种同样激进的确定性的陪衬,这种确定性建立在上帝自我启示的直接(direct)和无媒介的(immediate)行动之上(单义性)。
对巴特来说,认识上帝与认识配偶不仅涉及不同的认识对象,认识上帝也是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认识。这并不同于更正教经院主义学者所表述的,即上帝的知识和上帝的存有与受造物在性质上(而不仅仅是数量上)不同。对普罗提诺(Plotinus)来说,上帝是“超越存有”(beyond being)的,而对巴特来说,上帝是“全然他者”,若是如此,人类便没有认识上帝的自然能力。否则,就会朝向伯拉纠主义或至少是半伯拉纠主义(如卡尔·拉纳[Karl Rahner])。然而,我认为巴特(否认任何自然能力)和卡尔·拉纳(肯定自然能力)都未能区分自然能力和道德能力。改革宗正统神学断言,即使在堕落之后,人类认识上帝的自然能力仍然完好无损;人类失去的是认识上帝的道德能力。使人真正成为人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失去;相反,是整个人的存有都被罪所俘虏。因此,恩典更新并解放自然,以实现其命定的目的。
然而,巴特没有做出自然无能和道德无能之间的这种区分。这样,全然败坏就很容易与人类的自然状况相混淆。在启示事件下,上帝不仅要克服我们道德上的堕落,同时还要克服我们自然的有限性。上帝的自我启示本身从无到有(ex nihilo)地创造了这些能力。这种自我启示与我们所认识或经历的任何其他事物甚至连类比的对应都不存在。“上帝和祂的话语以不同于自然和历史实体的方式赐给我们……但是没有人类认识可以与此上帝言说相对应……在此上帝言说中,上帝和祂话语的知识是通过‘上帝与我们同在’(God with us)实现的。”[23]有罪的人类无法预测、预备或掌握的那完全令人惊讶的福音内容,导致巴特进一步更为激进地宣称,福音临到我们的形式与我们普通的自然能力是不可通约的(incommensurable)。这样,启示事件除了打开被罪蒙蔽的眼和对上帝声音充耳不闻的耳之外,还在其发生时创造了自己的眼和耳。与其说是恩典恢复自然,倒不如说是恩典取代了自然。
如果说自然主义的更正教将“上帝”简化成了自然和历史的进化,巴特则很难想象什么东西可以在无条件的意义上被称为上帝的话语,同时又完全是人类的话语。上帝不通过水、饼和酒工作:他认为称这些为“恩典的途径”(means of grace)是该受谴责的[24]。我们可以通过做这些事情作为对上帝恩典的回应,但在巴特对圣礼问题的处理中,受造性的媒介变得格外值得怀疑。例如,当巴特将符号(水的洗礼)与其所指(圣灵的洗)严格分开时,我们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将在下面详细说明这一点。
托伦斯(T. F. Torrance)同样把人类对上帝的认识说成是“神秘”而“出于直觉的”。[25]这种启示无法在语言或逻辑上具体说明,但根据托伦斯的说法,我们确实通过它与基督相遇。巴特学派似乎不愿意将上帝的话语与物质性的媒介相提并论,无论是在其圣经论,还是(至少对巴特来说)在其圣礼论中都是如此。在这方面,它延续了现代(实际上是西方)对“符号–所指”关系(换言之,也就是媒介)的怀疑主义遗产。除了“普罗提诺式”的极端超越性,人们还发现了一种唯名论的极端内蕴性(hyper-immanence)。这与我上面所说的一点有关,即巴特的辩证思维中极端超越性(他思想中批判性的一面)和极端内蕴性(唯实论的一面)并存的张力。在第一种模式中,他接近多义性,而在第二种模式中,则接近单义性,而我在上面(与更正教正统一致)指出,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一直是类比性的。上帝与人类之间的类比关系(“是”又“不是”)肯定了上帝的无限超越性(即差异)同时又不否认显明的相似性,而与此不同的是,巴特遵循单义性的辩证思想,将上帝定义为与有限的现实相对。
当然,康德将这个难题推向了逻辑一致的结论,而施莱尔马赫试图通过诉诸共同体经验来绕过它。巴特勇敢地与那立场决裂,但我们很难抗拒这样的印象,即对他而言,启示仍然占据着非理性的领域。他的实动主义至少部分是唯名论对意志的强调的残余。甚至逻各斯(Logos)与人性在基督位格上的联合,也是每时每刻由一个意志的行动所决定。[26]事实上,巴特自己做出这个联系:
同样,在作为人类语言的圣经和上帝的话语之间,完全不可能有直接的同一性,因而在受造物本身的现实与造物主上帝的现实之间也不存在同一性……这甚至在基督的位格上也不能发生。在我们所面临的所有独特性和不可分割性中,在基督身上上帝与人之间的等同是一种自取的等同,一种由上帝特别意愿、创造和影响而有的等同,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是间接的,也就是既不在于上帝的本质,也不在于人的本质,而取决于上帝对人的决定和行动。我们必须考虑这些内在的差异,而这对圣经中上帝的话语和人的话语的统一性来说也是一样的。[27]
与对他人的启示论和圣经论的回应类似,巴特关于上帝和上帝与世界关系的教义(而不是他可能从自由主义继承的任何特定理论)作为底层的理论基础常常被批评家所忽视。根据上帝的决定,这些人的话语成为上帝的话语。圣经“也可以而且必须——不是像耶稣基督那样,而是在与耶稣基督同样严肃的意义上——被称为上帝的话语:确切地说,是使用人的话语符号的上帝的话语”[28]。基督的人性“是首先和最初的符号”,此后按照尊贵的顺序依次是圣经和宣讲。[29]巴特的启示论不能通过试图将其定位在从自由主义到正统神学的光谱上来赞赏或批评。一种特有的本体论(由此产生一种对符号–所指关系的特有说明)产生了巴特关于话语的教义。
巴特的实动主义在他的本体论中占有主导性地位,不能简单地用唯意志论(voluntarism)的谱系来理解。然而尽管如此,这种比较仍旧具有启发性。中世纪晚期思想家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切断了符号与其所指之间的联系,因此他能够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信仰是对圣经和教会权威的认可——是一种非理性的飞跃,与信仰和理性,以及真理和证据之间任何可观察的联系都没有特别的关系。尽管理性和感官经验本身对于研究具体的事物(例如自然科学)是足够的,但信仰却是盲目的顺从。把唯名论的这种强调与巴特的强调放在一起,我们就会发现,巴特克服现代性的总体战略似乎没有初看起来那么成功。唯名论强调符号与所指、信仰与理性、智识与意志,探索与对权威的顺从之间的割裂,而巴特强调通过历史、智识、语言和文化的媒介接受启示的自然无能,而不仅仅是道德无能。
当论证圣经在上帝选择的地点和时间成为上帝话语时,巴特并不是(如一些巴特主义者和反巴特主义者经常建议的那样)认为它变成了不同于其本质的东西。为了理解巴特的意思,我们必须明白前文已经总结的哲学预设。在他看来,启示永远是一个事件,绝不是我们可以拥有的人造之物——甚至圣经也不行。“我们不能拥有启示‘本身’。”[30]圣经“是对上帝启示的见证,但这并不意味着上帝的启示如今以任何已完成(divine revealedness)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圣经不是一本预言之书;它不是直接启示的工具”[31]。虽然巴特雄辩有力地谈到圣经是启示的主要见证,但他对将圣经视为启示的方式持谨慎态度。否则,他认为,启示将成为一个已然被给予的、被拥有的客体,而不是一个主体——即上帝的自我启示。
改革宗传统肯定了在宣讲和圣餐中符号与所指的联合,而“慈运理派”的观点则倾向于切断这种联系,将符号简化为纯粹的人类证言(testimony)或见证(witness)。如果说某些保守派近乎要用一种更正教的变质说将圣经与上帝的本质等同起来,那么巴特的观点似乎使得圣经(如同圣礼)仅仅能够提供人类的见证。
换句话说,巴特的“上帝中心论”(theocentrism)还不够以上帝为中心:“间接启示”意味着在圣经、宣讲和圣礼中,不是上帝通过人类使者来到我们面前说出他的话语,而是人类见证人作为反思者,而非实际上作为那话语的承载者来到我们面前。这绝不应该与人类语言的“符号性”观点相混淆。巴特对此是相当明确的:“言说不是一个‘符号’(如蒂利希所认为的那样)。”[32]他也没有暗示启示发生在自然的、历史的事件之外——甚至连道成肉身也证明了这一点。[33]然而,“它首先暗示了上帝圣言的属灵本质,完全不同于自然的、肉体的或任何物质性的事件”[34]。如果想了解巴特启示论的背景,我们应该读慈运理,以及赫尔曼和克尔凯郭尔。巴特甚至谈到了“上帝的话语的上和下两个方面”[35]。我认为,这种以二元论的方式讨论符号与其所指,是如此多的对“上帝–世界”关系和媒介的历史反思的祸根。
巴特对启示和圣经的截然区分也源于他的“启示即和好”(revelation is reconciliation)的观点。通过先知和使徒对基督的主要见证,上帝的话语本身(基督)就是上帝的启示与和好。“圣经(如今)被认为是上帝的话语(通过信心),因为它是上帝的话语”,故此对教会有权威。[36] 当圣经成为上帝的话语时,它只会成为其已然所是的,然而除非上帝愿意,否则它不会在任何特定情况下,向任何特定的人成为上帝的话语。我们再次发现了巴特在彼时彼地的启示(revelation),与此时此地的光照(illumination)之间的混淆。如果说巴特过度地割裂了符号和其所指,那么他更是将启示和光照之间的任何区别都彻底地瓦解。成为启示的对象就是“得救”。巴特明确指出,圣经“不是因为我们相信它而成为上帝的话语,而当然是因为它成为向着我们的启示”[37]。它的存有是在行动中。正如逻各斯通过每时每刻的决定而维持在耶稣基督里与人性的联合,上帝的话语与圣经和宣讲的重合始终是一个上帝决定的事件。“上帝的话语就是上帝本身”。[38]
又一次,一个重要的本体论区别被瓦解:上帝的自我启示被简单等同于上帝的永恒本质。如果人们在这种混淆中跟随巴特,当然就绝不能轻易地说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不敬拜一本书。因此,巴特的结论不是源于对圣经的轻看,而是源于一种关于启示的本体论,这种本体论不允许任何人的东西成为启示本身,而最多只能作为启示的见证。以一种“聂斯脱利主义”(Nestorian)式的方式,上帝的话语在一处,而人的见证在另一处。后者与前者的间接一致总是上帝一个新的决定的结果,是祂意志行动的一个新事件。诚然,功能主义或工具主义的启示论比巴特更进了一步,但当巴特拒绝直接将上帝的话语与人类的话语等同起来时,这种观点已经成为了可能。
此外,对巴特而言,圣经属人的特性不仅意味着有犯错的可能,而且还意味着“在圣经中也许只是单纯相信上帝的话语,即使它与我们相遇不是以我们称之为历史的形式,而是以我们认为必须称为神话(saga)或传说(legend)的形式”[39]。事实上,“圣经的脆弱性,即它的犯错能力,也延伸到它的宗教或神学内容上”[40]。他在这段话中再次补充说,这是圣经确实是人类见证这一主张的必要前提。再一次,克尔凯郭尔式的时间和永恒的辩证在巴特的如下陈述中显而易见:
像亚伯拉罕和摩西这样的人物,他们是否是后来神话的产物有什么重要呢?——谁愿意相信就那么相信吧!在他们之前或之后的世纪里,曾经有过像亚伯拉罕那样凭信心生活的人,像以撒和雅各那样在应许之地做客旅、清楚地宣告他们正在寻找一个家乡的人,像摩西一样看见那位看不见的主就因此忍耐的人。曾经有过勇敢的人。[41]
换句话说,真实的历史并不真正具有决定性:具有决定性的是这些人所见证的永恒真理。历史上的时间性事件只不过是已经在永恒中决定性地发生的事件展现出来而已。
我们或许可以相信那些我们能够相信和愿意相信的事,这些事鼓舞人们去冒险,激励那些看见和听见的人,但我们不能否认所有这些人(无论是有名字的、没有名字的,以及假名字的)被卷入的那运动本身,就像我们不能否认星辰苍穹围绕一个未知的中心恒星旋转一样。
它们都是标记,指向远离自己的事物。[42]在启示中问题“不在于历史而在于真理”[43]。“旧约和新约中的圣经历史根本不是真正的历史。从上面看来,那不过是一系列自由的上帝的行动;从下面看来,不过是一系列徒劳无功的尝试,想要去完成一些本身并不可能的事。”[44]
尤其是鉴于当时“宗教历史”(history-of-religions)学派的主导性的方法,巴特的辩证历史观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挑战,它承认救恩是一个神迹,而不能由内蕴性的规则和过程予以解释。然而,巴特的观点却并没有足够严肃地对待圣经在上帝的末世性的纵向行动与其在历史中的横向展开之间建立的那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巴特的体系中,末世论总是处于吞并历史的边缘。尽管一再批评布尔特曼(Bultmann),巴特并没有完全摆脱他的导师们(尤其是赫尔曼)的诱惑:
不管历史上的耶稣如何,可以肯定的是,耶稣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既不属于历史学,也不属于心理学;因为历史和心理的东西都如此易朽烂。基督的复活,或者说祂的第二次降临(两者是同一件事),不是历史事件。[45]
很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巴特说复活“不是历史事件”,这并不是在暗示复活没有在历史中发生。相反,他否认复活属于历史学;换句话说,否认复活可以通过历史调查予以解释。它发生在历史中,但不属于历史。巴特相对而言缺乏对历史的关注,这使得他将复活和基督再临压缩为了单一和相同的事件。“新时代的曙光,那昔在、今在、以后要来者的主权性统治的曙光——这就是复活节的意义。”[46]再一次,巴特有益地提醒我们末世论的重要性,但他的末世论似乎吞没而不是决定了历史本身的方向。
与此同时,巴特可以称圣经为上帝的话语,是因为它可以成为启示事件的契机。我们或许可以谈论逐字默示,但不能谈论一本被逐字默示的书(即“完成的启示”)。[47]巴特认为改教家们教导的是,圣经的内容构成了其作为上帝话语的权威。[48]然而,他控诉宗教改革后的神学家们妥协了上帝的主权(即祂的话语高于圣经),而将默示简化为一种可见的、可识别的属性(在书中固有的属性):这是一种自然神学。[49]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巴特的指控恰恰导致了相反的结果:圣经被简化为了一本自然之书,其历史细节可以被任何人辨识。
可以理解的是,启蒙运动遵循了这一预设,只是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巴特称:“加入十八和十九世纪的狼群而攻击十七世纪的默示教义,如果是因为其中明确的超自然主义,这是没有意义的。相反,我们必须攻击它,是因为它的超自然主义还不够彻底。”通过假定圣经无误(正如初代教父们也倾向于如此),更正教正统使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可以掌握的东西,这“抹煞了上帝话语的实现只能是其自己的决定和行动这一观念”。巴特补充说:“因此,我们必须将十七世纪的默示教义当作错误的教义抵制和拒绝。”[50]同许多现代神学家一样,巴特似乎是从零散的引文而不是从对资料来源的仔细研究中,收集到了他对更正教正统的圣经教义的解释。虽然本文的篇幅不允许我对此进行反驳,但巴特在这一点上将改教家与他们的继承者区分开来的可疑尝试——这在当代神学辩论中司空见惯——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误解,即更正教正统将逐字默示等同于机械默示(即听写)。[51]
在巴特看来,更正教正统教义及其“幻影论式”(docetic)的对上帝话语的认识,与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及其“伊便尼式”(Ebionite)的理解不过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将圣经视为一本书,可以脱离其内容而判定其性质。[52]破解这个僵局的唯一方法是承认谈论上帝的话语“不是对一个状态或事实的思考,而是观看一个事件,一个与我们相关的事件,一个作为上帝的行动的事件,一种基于自由决定的上帝的行动的事件”。[53]上帝的话语永远是一个新的事件,是上帝的一个新的工作,而不是属于历史的某种东西。[54]神迹在于,甚至借助和通过有罪却被上帝拣选、呼召、称义和洁净的受造物的可谬言语,上帝在说话。[55]“因此,如果我们认真对待这个事实,即这神迹是一个事件,我们就不能将上帝的话语在圣经中的临在,视为这本书本身,以及我们面前的这些书卷、篇章和经文的固有和永有的属性。”[56]
在我看来,巴特对此问题的处理寻回了改革宗对“圣礼性的道”(sacramental Word)的一个重要强调——即上帝的话是“此时此地”的一个事件,在该事件中,圣灵外在地呈现基督,同时内在地光照我们以接受祂。然而,巴特并没有充分公正地对待正典的本体性地位,即作为上帝的默示过程的产物。需要再次说明的是,这不是巴特“轻视圣经”的结果——仿佛圣经论是一个孤立的岛屿——而是一种实动主义的本体论导致的启示论。至少在我看来,这种教义同时过于具有唯实论(单义性)和理念论及批判性特征(多义性)。甚至圣经都没有让我们接触上帝的原型知识,而是适应的(accommodated)、类比的(analogical)、摹本(ectypal)的描述。然而,那有限的、受造性的、媒介性的知识却可以与上帝的自我启示本身相一致。因此,不管有多少缺陷,巴特的圣经论并不是由自由主义的原则性预设所驱动的。尽管巴特接受了福音派坚定拒绝的一些高等批判的结论,但他的基本假设是(如果存在的话)实际上的极端加尔文主义(hyper-Calvinistic)。巴特的主要动机是对上帝的主权、超越性和作为全然他者的强调,而不是任何对人性的赞美。巴特所拒绝的类比本体论和认识论不仅是初代教会和中世纪神学家肯定的,也是更正教正统所接受的。这些改教家们的继承者一致认为,受造物以类比的方式有份于上帝,作为受造物,我们对上帝的知识是由相似性以及更大的差异性共同构成。上帝不是众多存有中的一个,而是一切存有的源头。因此,上帝和世界不能被归入一个共同的“存有”范畴,一端是上帝,另一端是世界。
在我看来,这种类比的方法使我们不需要屈服于非理性主义(多义性的怀疑论)和理性主义(单一性)之间摇摆不定的钟摆。启示是适应性的言说,甚至如加尔文所说,是上帝“必须远远低于祂的崇高”的“婴儿谈话”。[57]相比之下,对巴特来说,作为见证的属世话语(圣经),与发生于其中并通过其发生的崇高的“话语事件”之间存在着根本的脱节。简而言之,对加尔文来说,启示既不像在巴特的话语事件中那样崇高(单义性),也不像在巴特关于圣经的凡俗性概念中那样低微(多义性)。根据加尔文,即使在启示中,信徒也不会“达到(上帝那样的)崇高状态”,但我们确实会接受那“适应我们的能力,以便我们可以理解”的真理。[58]
鉴于我们已经探讨过的预设,巴特不仅想以上帝的主权为由肯定上帝不受创造(包括启示的人类途径)限制的自由;他还想避免一种静态的启示观。例如,奥托·韦伯(Otto Weber)有同样的关切[59]。这是正统改革宗神学家们同样关切的重要问题,他们强调圣经不是一本关于永恒教义和伦理教导的书,而是一部逐步展开的救赎戏剧。然而,关键的区别在于:在像霍志恒这样的改革宗思想家们从历史的角度看待这动态方面之处,巴特则是从生存论(existential)的角度看待。如前文所述,巴特担心将启示简化为历史进步(就像更正教自由主义那样),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他对经典圣约神学持怀疑态度。
问题在于,他将历史同化为永恒的倾向,是否使他避免了同样的弱点。经典改革宗神学将启示的动态性定位于其历史性和生存论两个方面:它在救赎历史中动态地推进,同时在审判和称罪人为义时是“活泼的,有功效的。”然而,巴特对历史动态性的警惕将他限制在了生存论方面。
类比的方法提醒我们,虽然我们所有的言语——包括圣经的言语——都远达不到上帝的崇高(排除单义性),但上帝却通过使用它来适应我们贫乏的能力(排除多义性)。藉着启示,我们“透过镜子观看上帝,模糊不清”,而不是“面对面”。然而,类比性的启示是真正的启示。既然上帝选择了适当的类比,我们就不必再选择自己对敬虔经验的表达,那种表达实际上不过是对我们自己心智(psyche)的展现(revelation),而不是对上帝的启示。值得注意的是,保守福音派(至少以卡尔·亨利为代表的福音派)一直同巴特一样抵制类比的教义,仿佛它是通往多义性的中途站,因此也成为通往认识论怀疑主义的中途站。[60]正因如此,这里提出的批评具有更广泛的相关性。
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巴特关于上帝在基督里的自我启示以及圣经和宣讲的大部分内容构成了一个强劲的挑战,使得教会再次成为聆听上帝说话的教会,但抹煞经典改革宗神学中的重要区分的做法引入的是混淆而不是澄清。我毫不怀疑,我们需要进一步反思启示的意义,而巴特也确实提出了不应忽视的重要议题。然而,归根结底,巴特或他的学生们还没有提供足以符合圣经自身主张的圣经论。即使像大卫·凯尔西(David Kelsey)这样同情巴特的解释者也得出结论认为:“在其他方面都相当不同的诸多神学立场达成了一致的批判性判断,即在新正统(neo-orthodox)时期发展的据称‘合乎圣经’的‘启示’教义,在概念上是不自洽的。”[61]
巴特的拣选论
巴特普救论倾向的驱动力,既不是柏拉图主义的归回神话(奥利金的“复原”[apokatastasis]),也不是自由派的乐观主义,而是我只能再次将其描述为“极端加尔文主义”的恩典教义。在传统改革宗神学中,一直存在着“堕落前拣选论者”(supralapsarian)和“堕落后拣选论者”(infralapsarian)之间的持续争论。前者认为,上帝拣选和弃绝的预旨在逻辑上优先于祂创造的预旨和对堕落的允许,而后者视拣选和弃绝为在逻辑上依赖于创造和堕落。
这个讨论的关键在于,上帝的拣选是针对被造的人还是堕落的人而作出。如果是前者(堕落前拣选),拣选是否还能被视为一种出于上帝恩典的行动,即从堕落的人类中选出一群被救赎的百姓?此外,堕落前拣选的立场难道不是使得加尔文主义更容易受到“上帝是罪的作者”的指控吗?在堕落后拣选的观点中,上帝在拣选和弃绝中的行动之间有明确的区别。由于选民是从已被定罪的人类中挑选出来,失丧者仅仅是不被包含在上帝的拣选中。他们只能责怪自己,而同时选民则只能感激上帝。然而,堕落前拣选主义者担心,如果上帝的拣选需要考虑到堕落,祂在拯救和审判上的主权将会受到损害。标准的改革宗和长老会告白明确或含蓄地支持堕落后拣选,尽管堕落前拣选从未被明确拒绝过。
尽管乍看之下这些区分似乎使得对更正教经院哲学的讽刺刻画更加可信,但巴特看到了这个辩论的重要性,并坚定地站在了堕落前拣选主义者的一边。然而,巴特再次通过他的辩证方法彻底修改了传统立场。首先,他拒绝任何与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行动不相符的、上帝隐藏的旨意的概念。巴特从基督的位格和工作揭示了上帝的普世性的拣选和拯救意愿的(可疑的)前提出发,他完全摒弃了奥古斯丁主义的共识,即上帝拣选了一些人而不是对全部人类施行救赎。其次,巴特使得基督而不是个人,成为了拣选和弃绝的直接对象。我认为,该举动是他一再倾向于简单地将人论崩塌为基督论的动机。从永恒起,基督被天父拣选成为被弃绝的儿子和被拣选的儿子。
结合以上两者,全人类都在基督里被拣选和弃绝。从人的角度看来,由人类存在的处境和可能性所决定,全人类都被弃绝;但在上帝看来,由恩典所决定,全人类都被拣选。此外,这拣选并不是鉴于堕落的人类处境而做出的。
因此,这个(双重预定的)奥秘涉及的不是这个人或者那个人,而是涉及所有人类。通过它,人类不是被分开而是被联合在一起。在双重预定的奥秘面前,他们都站在同一条线上——因为雅各永远同时也是以扫,在永恒的启示“时刻”(Moment)中,以扫也是雅各。当改教家们将拣选和弃绝的教义(预定论)应用于这个或那个个体心理上的整体时,当他们定量地指代“选民”和“被弃绝者”时,正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他们的看法带有神话色彩。[62]
巴特继续说道,毕竟:“一个在时间中的、可被观察的、心理上可见的个体究竟如何能够被永恒地拣选或弃绝呢?”
个体不过是一个舞台,一个在人的自由中,也就是说,安息在上帝里面并受祂驱动的个人的自由中,拣选和弃绝发生的舞台——这个舞台肯定不能再承受更多!我们已经知道这种在上帝中的二元性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它不涉及平衡,它是拣选对弃绝、爱对仇恨、生命对死亡的永恒胜利。[63]
柏寇伟合理地得出结论说:“巴特修订后的堕落前拣选主义阻碍了将决定性意义归于历史的道路。”[64]在巴特神学中,没有从忿怒到恩典的历史性过渡。[65]
巴特的拣选论可以被解释为寻找令人满意的神正论(theodicy)的现代尝试,这一直是思辨的诱惑。尽管巴特批评那种将上帝的话语变为哲学俘虏的做法,但巴特在许多方面都明显是一位思辨神学家。我意识到这说法似乎违反直觉,尤其是对一位如此明显地反对人类试图驯化上帝超越性的一切尝试的神学家而言。然而,鉴于新约经文以更为粗重的笔触强调人类会最终被区分为“得救的人”和“受诅咒的人”,我们还能有什么其他结论呢?巴特通过使得上帝的方式对人类判断(human judgment)来说虽不透明但至少令人满意,从而解除了上帝超越性的审判(transcendent judgment)奥秘。[66]
虽说上帝在隐藏中自我启示,但祂的内在本质却是在启示中单义而彻底地显明出来。上帝隐藏的旨意和显明的旨意之间不能存在区别。“这‘不’实际上就是‘是’。这审判就是恩典。这定罪就是赦免。这死亡就是生命。这地狱就是天堂。这令人敬畏的上帝就是慈爱的父,祂将浪子拥入怀中。”[67]
没有一种今天确定的拣选在明天不会成为弃绝,同样,也没有一种弃绝不会成为确定的拣选。唯一永恒的拣选是上帝的:历史和个体思想的倾向是次要和暂时的。[68]
在这里,辩证似乎完全屈从于矛盾。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克尔凯郭尔式的辩证(未解决的张力)屈从于黑格尔式的辩证(将“较低的”审判扬弃为“较高的”称义)。当然,弃绝和拣选是严格的对立或脱节(克尔凯郭尔的辩证法),但亚当和他的族群在更高的综合中被同化为了基督(黑格尔式的辩证法)。
这种新颖的预定论不仅影响了巴特对拣选和救赎教义的处理,而且为他的大部分神学奠定了基础。因此,巴特建议说:“我们的任务是解释‘是’和‘不’,以及通过‘是’来解释‘不’,同时不在确定的‘是’或‘非’中耽搁超过片刻。”[69]然而,这个辩证规则反过来则并不有效,因为正如我们在他之前的陈述中看到的那样,‘不’就是‘是’,审判就是恩典。归根结底,巴特表达的是如今已经普遍流行的观点,即圣经根本没有揭示那些拒绝基督的人的未来命运。然而,正如保罗·路易斯·梅茨格(Paul Louis Metzger)指出的那样:“布罗米利(Bromiley)回答道,大多数解经家与巴特的立场相反,他们坚持认为圣经对所讨论的该问题绝不是不可知的。”[70]
罗马天主教神学家、巴特的同情者和解释者汉斯·乌尔斯·冯·巴尔塔萨承认:“巴特的拣选论精彩地推翻了加尔文的拣选论,它强烈而持久地吸引了我;它与奥利金的观点相融合,因此也与‘阿德里安娜的圣周六神学’(Adrienne’s theology of Holy Saturday)相融合。”[71]巴特的“普救论”与奥利金的普救论在很多方面都相当不同,但它同样是推测性的和理性主义的。由于不能在解经的基础上证明,巴特为他的辩证拣选论辩护的唯一基础,是我此前描述的一系列他从哲学–神学观点中得出的预设。这是他从克尔凯郭尔式的脱节转向黑格尔式的综合的结果。我在这里的目的不是提供基于解经的反驳,而是指出巴特的拣选论与奥古斯丁以及福音派神学之间的这一根本区别,特别是指出他的结论是如何从我所考察的本体论预设中所得出的。
以他的拣选论为基础,“和好”只不过是这个永恒预旨的实现。末世论和历史彼此需要,但这是另一个“辩证屈从于综合”的例子,结果是前者同化了后者。启示就是和好。此外,“亚当”和“基督”并不是实际指代两个各自代表两个不同的人类群体的个人,在这两者中都没有上帝末世性的目的在历史中的展开。“亚当”代表了从上帝的恩典和人类顺服的最初关系到反叛的运动,而正如麦考马克所描述的那样,耶稣基督带来的是:“归回‘原初’(Origin)(即和解)。这两个运动不应被认为是接续发生的,而是并行和同时的。”[72]至少在这个程度上,巴特的拣选论可能比我上面建议的更像奥利金的复原论(doctrine of restoration)。
基本上,这里有两个方向——在我看来这两个方向都是错误的。第一个是将上帝与人类立约关系的线性历史发展同化为末世论。第二是将历史同化为特定类型的末世论,而正是因为其脱离了历史,这种末世论失去了亚当所受考验的动态未来导向。亚当不仅是为了保持顺服而被造,而是被赋予了一项使命,即把全地都带入到三一上帝的统治之下。这条路的尽头是最终的成全(consummation)——跟随创造主上帝从“六日”的劳作到永远安息的“第七日”。当这个计划被遗忘时(每当永恒吞没了时间,这种情况就必然发生),救赎的目标从本质上变成了重回起点,而不是超越人类在亚当历史中所知道的任何事物。“复乐园”(Paradise Regained)不同于成全,而后者只能用“超越的乐园”(Paradise Transcended)来形容。换言之,巴特的末世论还不够末世性。
因此,一方面,巴特的末世论吞并了历史,但正因如此,就远远没有新约圣经所启示的那样具有末世性。霍志恒认为,圣经末世论将永恒的垂直向量与时间的线性向量连接起来,如同一个三角形。然而,对巴特来说(正如在数不清的其他神学中一样),后者只是被前者所吸收(当巴特更倾向于黑格尔时)或被置于对立双方(当他更倾向于克尔凯郭尔时)。
巴特的教会论
克尔凯郭尔式的脱节在巴特的教会论中更为明显,尤其是他对圣礼的处理。他论及一些相当精彩的内容,即教会不是基督位格和工作的延伸,这是当代神学迫切需要听到的警告。然而,无论上帝做什么,都只是一个事件,而不在时间内延展。因此,对于巴特来说,经验中的教会(empirical church)不仅与基督和福音不同,而且也将缺席于最终的成全。“上帝的国”(启示的和末世性的)不仅区别于有形教会(历史的和暂时的),而且与之反对。教会的活动“与福音的关系仅在于它不过是一个由炮弹爆炸形成的弹坑,是福音显示其自身的空间”[73]。教会的言说和行动的“否定形式正是通往至圣者的路标”,其自身却绝不是圣的。[74]
事实上,巴特提到“以扫的教会”和“雅各的教会”——不是作为两个相互独立的实体,而是分别作为可见的教会和隐藏的教会。我们再次看到,当改教家坚持教会在这个世代是部分隐藏和部分可见时,巴特将可见的教会等同于以扫的教会:“那里没有神迹发生,因此,正是在人聆听和言说上帝时,人被显出是虚谎的。”[75]
上帝的工作和教会的工作处于根本性的、未解决的对立中(克尔凯郭尔式的辩证法)。甚至同圣经和讲道相比,施行洗礼以及分发饼和杯这类人的行动,更是无法与上帝的工作等同起来。它们只能是人对上帝在这些途径之外所做的事的见证、顺服和证言。巴特明确地采取慈运理而不是加尔文和改革宗传统的圣礼观,他甚至比这位苏黎世的改教家走得更远,否认圣礼是“恩典的途径”。我们再次看到,巴特这些所有的神学修订都与一种不恰当的本体论有关,这种本体论不允许在造物主与受造物、永恒与时间、灵魂与肉体之间建立真实的联合。圣礼是纯粹人的礼仪性的顺服行为。[76]正因如此,巴特坚持认为,在任何意义上,洗礼和圣餐都不能被视为圣礼或恩典的途径。事实上,最为强烈的对比存在于基督和基督徒的行动之间:“祂是祂,祂的工作是祂的工作,与之相反的是所有基督徒的行动,包括基督徒的信心和基督徒的洗礼。”[77]因此,洗礼面对一种危险,会被贬低为与其他的信徒敬虔行为一样的人的行动。
在挑战了认信改革宗的解释以及路德宗和罗马天主教的圣礼观之后,巴特认为教会的这些行动不是“奥秘的”或“恩典的途径”。“这种共识需要被去神话化。我们反对这个共识。”[78] 巴特承认所有的改革宗信条都拒绝慈运理将符号与其所指的事物分开的做法,甚至这种做法也被慈运理的继任者海因里希·布林格(Heinrich Bullinger)所起草的信条拒绝,而在巴特看来,那是“向加尔文圣礼观的方向……倒退了一步”[79]。巴特接受了“新慈运理主义者”(Neo-Zwinglian)的称谓,尽管他否认慈运理是其方法的来源,同时因为慈运理仍然坚持婴儿洗礼,巴特暗示这位苏黎世的改革者做得还不够彻底。[80]
巴特的异议的核心是“圣礼的联合”(sacramental union)这个概念——换句话说,受造物的行动可以成为上帝施予救恩福分的途径。显然,他的形而上学预设从一开始就很难肯定一种强有力的媒介概念,巴特认为这种概念必然会最终倒向新更正教主义的上帝与世界的同一。当启示仅仅被视为一个事件时,实动主义看起来特别像“偶因论”(occasionalism)——在这个事件中所有受造物的可能性都被暂停、搁置或克服[81]。
慈运理和巴特都没有认为讲道不能传递恩典。乔治·亨辛格将这种差异的大部分不是归因于慈运理,而是巴特自己的辩证基督论:“卡尔·巴特很可能是基督教教义史上第一位有意识地在‘亚历山大学派’和‘安提阿学派’基督论之间来回交替的神学家。”[82]同时,亨辛格通过诉诸巴特自己关于上帝的话语的教义,挑战他不愿将圣礼视为一种恩典的途径的观点:
巴特著名地拒绝将“圣礼”一词用于洗礼和圣餐,理由是耶稣基督本身才是唯一真正的圣礼。(他更愿意将它们视为“感恩的途径”而不是“恩典的途径”)。然而巴特在这里的逻辑似乎与他所采取的其他立场奇怪地不一致。因为虽然耶稣基督也是上帝唯一的话语,这并不妨碍巴特将圣经与合乎圣经的讲道作为上帝话语的次要形式……我看不出他为什么不能将洗礼和圣餐与讲道保持一致,以及将教会作为圣礼与圣经作为书面话语的观点保持一致。耶稣基督在严格和本有的意义上仍然是唯一而真正的圣礼,正如祂是上帝唯一而真正的话语。[83]
任何关于上帝的话和人的话的关系的表述,也可以应用于洗礼和圣餐的圣礼关系。
巴特的本体论假设再次发挥作用。上帝与世界的关系被认为是脱节的——这种区分在一种唯名论方向上总是处于打破“符号–所指”联系的边缘。这就是为什么书写下来的和宣讲出来的上帝话语不能直接等同于启示,以及为什么教会和圣礼只能见证而不能承载将来世代那现实的首要原因。这里的关键是改革宗神学与其他传统一起,确认符号及其所指之间的“圣礼性联合”时所表达的类比性的连接(analogical link)。正如加尔文经常指出的那样,每当圣经被阅读或宣讲时,我们都听到上帝在说话;通过施行圣礼时牧师的言语和行动,我们看见上帝在洗礼中向着我们和我们的孩童,以及在圣餐中向着我们的有效承诺。这样的人的职分不仅仅是作为圣灵主权性行动的场所,也是圣灵通常用以完成该工作的途径。
与巴特强调上帝的绝对自由和超越相关的,是他对“非位格–归入位格”(anhypostatic-enhypostatic)基督论的多少有些奇特的表述,他把这种表述归于他对改革宗经院哲学的阅读[84]。巴特的表述更倾向于“话语–肉体”(Word-flesh,亚历山大学派)而不是“话语–人”(Word-man,安提阿学派)的基督论(借用凯利[J. N. D. Kelly]的概念),这在形式上是正统的,但是像亚他那修一样,他很随意地朝着亚波里拿留主义(Apollinarian)的方向漂移。”[85]这是因为他独特的构建:“隐藏–显现”的辩证法。根据该辩证法,主体是上帝,而遮盖是耶稣。就像在亚历山大学派中一样,这里似乎有一种幻影论(docetizing)倾向,当这种倾向达到极致(基督一性论[monophysitism])时,人性将被吸收到神性中(这是因为,若不仅仅是理解那无限者,而是要直接显明那无限者,人作为人本身是无法完成的)。巴特说:“正因为祂是上帝的儿子,所以祂才是真正的人。”[86]但是基督独特的人性——不仅是人性本质本身,还有这个特定位格者的生活和事工——能被如此轻视吗?这不是将人性同化为神性吗?
再一次,关键问题是,启示和救赎事件是否可以完全归因于上帝,但同时通过受造的媒介完成。与此同时,正如梅茨格借鉴麦考马克所指出的,当巴特认为“上帝的话语(divine Word)在祂的道成肉身中,一刻不停地通过意志取得人性”时,他在安提阿学派的方向上比改革宗走得更远。[87]在这里,一种激进的唯意志论遇到了一种同样激进的实动主义,可以说,即使神性和人性的关系已经从“上头”得以确立了,这种实动主义仍旧对两者的认同过于怀疑。
藉由巴特,越过巴特
如果我们和巴特之间有问题——我认为我们依然应当如此——并不是因为那呼喊,而一定是由于其他原因。那呼喊是先知和使徒的呼喊,是殉道者和改教家们的呼喊。当美国福音派的许多人沉醉于人类自身和荣耀神学时,那呼喊是见证者的呼喊,它所指向的不仅是离开呼喊者自己,也离开人类自身的所有可能性——甚至是教会——而指向那一位启示和拯救的上帝。即使巴特自己也承认他的神学中回荡着十九世纪新更正教主义的声音,但他对上帝和上帝恩典的重新发现,简直是划时代的。
在我看来,自由派与保守派、现代与后现代,甚至“巴特主义”与“正统”之间的对比从来没有让我们走得太远。虽然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标签及其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和所造成的深远影响仍然在某种程度上有效,但我更感兴趣的是以与普世信经和改革宗信条一致的方式做一名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很多保守的讲道似乎忽略了一个要点:基督在祂的拯救职任中被呈现在饥渴的灵魂面前。这些灵魂在假定的自主性中对人性奉承,而不是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上帝。巴特在反击一直富有吸引力的伯拉纠主义异端方面其实做得很好。就巴特宣讲了那消息而言,他应该受到赞赏和尊重;就他偏离那消息,或者没有充分放弃现代性预设而言,他应该被倾听和批评。
当然,问题是从哪种立场可以证明这种批评的合理性。虽然唯独圣经具有实质性的权威,成为(对这批评的)绝对规范,但普世信经和改革宗信条提供了以改革宗的方式确认基督教信仰意味着什么的持久定义。即使在更为保守的圈子里,“改革宗”这个标签也正在变得富有弹性。它越来越不再由其追随者所认信的具体内容来定义,而是由个人或群体认为合适的某些教义或特定强调来定义。问题不在于巴特是通过自我认定还是教会成员的身份而归属于改革宗,而是在于他的教义是否可以被恰当地描述为改革宗。用其自身的认信来定义改革宗的信仰和实践并不是傲慢;傲慢的是允许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把自己凌驾于群体之上,按照自己的亮光来定义它。应当定义我们共识的是教会,以公开地、共同体的方式认信基督教信仰;而不是一个派系,依赖其主要领袖以及他们的著作。
当论到什么可被认为是真正的“福音派”时,问题又要复杂得多。毫无疑问,巴特自己的定义比近年来提出的许多定义都更具限制性。例如,斯坦利·格伦茨(Stanley Grenz)认为福音派身份应当由虔敬(piety)而不是信经和信条来定义。[88]事实上,他对圣经和教义在基督教信仰及实践中的作用的描述,至少在我看来,与乔治·林贝克(George Lindbeck)所说的“体验式表现主义(experiential-expressivist)”的观点没有区别。正如我在别处讨论过的那样,鉴于福音派是由各种支流汇合而成的这一历史事实,我认为很难挑战这类定义。[89]
尽管宗教改革的溪流雕刻了深深的峡谷,但虔敬主义的支流至少不比后宗教改革正统神学更少(或许更多)地塑造了英美福音派,而复兴主义又在很大程度上侵蚀了改教家的大部分遗产。如果与查尔斯·芬尼(Charles Finney)的遗产相比,巴特的遗产就算是积极健康的了。巴特写道:“慈运理和加尔文在天主教面前摆出的同一阵线,一百年后由多特会议中抵挡阿米念派主义的父兄们捍卫,这其中一定有某种意义。但今天,细心的观察者在哪里不会发现阿米念主义的教义被视为理所当然呢?”然而,如果人们发现自己亲近这种预设,就必须问:“作为改革派教会成员,我们有什么权利和目的站在反对教皇的一边?”[90]此外,巴特和他的继承人可以被视为我们的盟友,进行一场定义教会及其使命是与福音,而不是与世俗风潮相关的战斗。鉴于今天的“福音派”含义,真正的问题也许不是巴特是否值得,而是他是否愿意被纳入到这样的运动中。
由于福音派的教导缺乏正式的共识,我无法诉诸于其他更具决定性的内容,而只能使用从一些福音派机构和委员会具有代表性的声明中获得的印象。这些声明表明一些福音派领袖至少试图通过如下方法定义该运动,即:忠于历史性的基督教,重视基督和圣经,肯定唯独恩典的救赎、重生的必要性以及基督的身体性再临。
在所有这些方面,巴特肯定会得到高分——再一次,高于今天引起我们关注的不少福音派思想家、牧师和教会运动。近年来,福音派越来越多地(至少在实践中)远离圣经的权威,而倾向于巴特所称的“自然神学”,使得人类科学、营销哲学、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神话往往同上帝活的话语耶稣基督一样,被视为启示。巴特谴责蒂利希的“关联法”(method of correlation),但“后保守主义”(post-conservative)福音派将文化视为神学的来源之一。[91]”例如,约翰·弗兰克(John Franke)呼吁将巴特作为改革宗神学未来的主要典范,但他似乎对蒂利希至少同样感兴趣。[92]巴特教义学核心的内容——基督已经成就的工作的绝对客观性——在弗兰克对福音与文化之间关系的描述中被推到了后台。神学的任务与其说是重新聆听那作为颠覆性言说的福音,这福音于每个世代“在我们以外”(extra nos)临到那不敬畏上帝之人,倒不如说是促进福音与文化之间“道成肉身式”(incarnational)的交谈。正如劳拉·斯密特(Laura Smit)在论到加尔文的观点时提醒我们:“我们对上帝的所有认识都是借由媒介而来,(但)他相信不是由文化处境作为媒介,而是由上帝自己向着我们的处境。”[93]
虽然弗兰克对“关联主义”(根据蒂利希、考夫曼[Kaufman]和特雷西[Tracy])和“翻译”(如在福音派的处境化宣教中)提出了一些合理的批评,但“它们结合起来指明了前进的道路”[94]。弗兰克补充说:
鉴于两者的解释性和被建构的本质,福音和文化都不能作为两者对话的主要实体;我们必须认识到,神学是通过涉及福音和文化的持续对话而出现的。[95]
正是这样的表述使得巴特惊恐而颤抖。
巴特预示着“非基要主义”(non-foundationalist)的议程,因此显而易见地适合成为反对现代性的资源。然而,与我在下面提到的那篇由明确的巴特主义者(乔治·亨辛格)写作的文章不同的是,弗兰克在整卷神学方法论中没有一次提到过凯波尔或者巴文克。他与斯坦利·格伦茨合著的那本较早的《超越基要主义》(Beyond Foundationalism)也是如此[96]。为什么像乔治·亨辛格和约翰·韦伯斯特这样的巴特主义者因为改革宗正统在后现代背景下为基督提供了确信的见证,而似乎更欣赏这些资源呢?
当巴特开始准备他的哥廷根讲座(Göttingen lectures)时,他对自己所接受的训练竟然会跳过更正教正统的丰富遗产而表示惊讶。新更正教主义(即自由主义)试图不断通过新的提议来“挤着穿过”这一时期,但这些提议实际上只不过是“启蒙运动和虔敬主义的新混合”。然而,巴特意识到:
只有我们先学会阅读作为教会教师的改教家们,并与他们一起阅读那作为教会的存在和本质的圣经,并从中询问教会科学(Church science)可能会是什么,我们才能取得成功。这恰恰可以,不,这必须从更正教正统早期的神学家那里学到。[97]
巴特这样告诫他的学生:
即使你后来可能决定与几乎塑造了所有现代教义学的伟大的施莱尔马赫革命走在一起,但我的迫切建议是,当你学习这门课程时,首先要学习和思考老一辈作家那固守不变的教义学,然后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98]
根据巴特自己的回忆,接触改革宗经院哲学为他提供了资源,使得他能够以超越“明显的胡说八道:施莱尔马赫以及在他后面蠕动和飞行的一切”的方式重新构想神学。[99]他哀叹道:“人们普遍认为教义学导论是必要的,有时以所谓的宗教哲学的形式出现,这表明我们没有生活在神学的古典时代。”[100]
在我看来,卡尔·亨利的巨著《上帝、启示和权威》(God, Revelation and Authority)[101],虽然在某些方面对巴特关于圣经权威相关内容的所有文献进行了仔细地阅读,但他提供的替代模型也同样不令人满意。这至少对我们这些坚持传统更正教对原型知识和摹本知识的区分,并且拒绝将真理的概念完全简化为命题陈述的人来说是如此。目前,福音派神学似乎被迫在卡尔·亨利和卡尔·巴特之间做出选择,而后者作为“后自由主义”主流与“后保守派福音派”之间的折衷选择,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福音派神学家和牧师。我认为,这里所缺少的是对经典改革宗传统的批判性对话,即使是在自称改革宗的福音派(无论是保守派或进步派)中也是如此。在巴特主义者那边有一个很值得关注的例外:乔治·亨辛格著作中的一章,题为“福音派和后自由派可以向彼此学习什么?”[102]
虽然卡尔·亨利的构建过于依赖现代性,但亨辛格指出:“其他与亨利所关注的相当不同的表述在福音派中也占有地位,这些表述坚持强有力的‘无误’教义,而没有亨利的过度的现代主义倾向。”他补充说:
与卡尔·亨利所代表的倾向相比,我特别认为亚伯拉罕·凯波尔和赫尔曼·巴文克的观点为福音派与后自由主义的富有成效的对话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为了不使得自己太容易,我不会遵循杰克·罗杰斯[Jack Rogers]和唐纳德·麦金[Donald Mckim],而是遵循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小理查德·B·伽芬[Richard B. Gaffin, Jr.]对凯波尔和巴文克的解释,后者对罗杰斯–麦金的解释进行了全面的修正和批评。[103])
亨辛格同意:“总体来说,许多后自由主义者对圣经统一性、权威和默示的描述,至少可以说,到目前为止都还相当薄弱和无法令人满意。”[104]卡尔·亨利被一种将真理缩减为命题性断言的单义性观点所驱动,而这些命题性断言“能够以一种价值中立的方式被认识,而不受任何自我包含(self-involving)的观点或命题所影响”,但亨辛格指出,还有一个植根于改革宗正统的福音派传统[105]。
与后自由主义相临近的第一个领域是凯波尔的观点,即“忠实阅读圣经的前提是圣经的统一性,而不是独立于信心的逻辑推理”[106]。其次,对于凯波尔和巴文克而言,圣经的统一性不像亨利认为的是“理性的统一”,而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统一[107]。因此,按照亨利的方法,命题内容同个人与基督的相遇是分开的,而在凯波尔和巴文克那里,两者被紧密结合在一起[108]。第三,就事实性而言,存在一个有趣的趋同:
根据理查德·伽芬,对这两位神学家来说,“圣经记录都是印象主义的;也就是说,圣经记录并不以公证的精度、蓝图,或者建筑的准确性为特征。”圣经记录并不意图传达“历史、纪年、地理数据……本身”;相反,它们试图证明的是“在基督里倾倒在我们身上的那真理”[109]。
第四,尽管他们甚至在历史细节上都坚持圣经的无误性,“伽芬写道,‘他们都认为,将圣经无误性推到聚光灯的中心是从理性主义者开始的那种知性主义(intellectualism)’。”[110]
根据加尔文,我们在圣经中辨别出一种模式——他指的是“那些最有助于理解基督的特征的屏幕图像”[111]。
因此,关于福音派可以从后自由主义者那里学到什么,我想建议的就是这点。尽管在这些问题上,福音派可能不愿意像弗雷(Frei)和林贝克那样走得那么远,但他们至少应该准备走到加尔文、凯波尔或者巴文克的位置。摆脱过度现代性的束缚,真正的对话就可以开始。[112]
亨辛格认为,耶鲁后自由主义的“文化-语言学实用主义”(cultural-linguistic pragmatism)对许多后保守主义福音派有吸引力,但“最终与其说是‘后自由主义’,不如说是‘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因为实用主义一直是自由主义的惯常选择”[113]。在这里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位巴特主义者,他鼓励福音派更多地关注加尔文、巴文克和威斯敏斯特,而不是弗雷和林贝克。忠于宗教改革“五个唯独”,以基督“在我们之外”的拯救工作为中心的福音派信仰,能够为教会的更新提供丰富的资源[114]。当谈到凯波尔、巴文克以及耶鲁后自由主义者时,“对单义性的拒绝区分了他们与像亨利这样的人,正如对充分性和可靠性的肯定区分了他们与现代怀疑论者”[115]。
结论
见证、证词和殉难不是通过“关联法”产生的。将神学作为圣灵引导下圣经与文化之间对话的产物,将圣经和文化都视为福音启示的媒介,这样的做法已经被尝试了一遍又一遍。施莱尔马赫、里敕尔、哈纳克和赫尔曼都是其中最伟大的例子。没有人会因为教会见证自己的自我理解、宗教意识或共同体语言及实践而迫害教会。世界对于让不同的共同体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中寻找到意义、身份、希望、灵感和疗愈毫无意见。基督徒总会遇到艰难,不是当他们试图在自己所属的时间和地点内展示其宣告信息的相关性和情境性时,而是当他们对现实本身的性质作公开而普遍的宣告时。这种遭遇总会产生出与对话同样多的冲突。
无论巴特自己的圣经论有怎样的缺陷,他的神学工程至少在这一点上代表了现代神学史上的哥白尼式革命:用彻底的“上帝为中心主义”(theocentrism)对抗新更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使得上帝的主动性被再次看见。上帝不仅决定答案,而且规定问题。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挑战巴特关于上帝话语的教义,但是当谈到神学的来源时,我们都会同意:圣经,而不是教会或文化,才是 norma normans non normata(“用于规范的规范,而本身不被规范”)。
借用虔敬主义的遗产,斯坦利·格伦茨和其他后保守主义福音派的捍卫者们关于圣经和教义的观点与巴特主义相比,更像是施莱尔马赫主义。巴特直言不讳地谈论罪和恩典,而现在的福音派神学和讲道则倾向于用功能障碍(dysfunction)和恢复来表达同样的观念,并且通过祂的爱“道成肉身”和改变生命来扩展基督的使命。巴特深信,人类无法为自己的救赎做出任何贡献,只能依靠上帝怜悯的主权性行动。相比之下,福音派越来越多地被一种实用的伯拉纠主义所淹没,这证明了朋霍费尔(Bonhoeffer)的评价:“美国基督教是没有宗教改革的更正教。”今天,越来越多的福音派神学家和从前的自由主义一样,对基督替代性救赎(substitutionary atonement)的教义感到不安,而与此同时,乔治·亨辛格、唐纳德·布洛施、威廉·普拉彻(William Placher)、乔治·林贝克和其他巴特的学生和崇拜者则在为之辩护。
今天的一些福音派基督徒对其他宗教表现出了更大的开放态度,将其作为救赎启示的来源,而将福音理解为效法基督的榜样(这当然与其他宗教和宗教人物或道德楷模之间有相似之处)。无论我们如何看待巴特朝向普救论的“乐观”倾向,这种倾向都是基于他对上帝拣选和恩典的认识,并且以基督为唯一基础。换言之,与美国福音派中一直蓬勃发展的神人合作(synergistic)的救赎论相比,宗教改革的神恩独作(monergism)有巴特作为其勇敢的捍卫者。在一片“没有宗教改革的更正教”土地上,巴特确实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声音。尤其是若非如此就只有自由主义或基要主义可供选择时,我加入了赞赏者的行列。自由主义和基要主义这两种运动彼此之间的共同点(即敬虔主义传统)比两者中任何一个与宗教改革基督教的共同点都多。认信改革宗基督徒可以从巴特和他的继承者那里学到很多东西。然而,我仍然相信,在两条道路彼此分歧的地方,巴特和他的继承者们代表的是一种倒退,而不是伟大的宗教改革遗产的更新。巴特仍然是一位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既不能被轻视,也不能被不加批判地接受。无论是好是坏,他的声音仍然与我们息息相关。
[1] 本文出自David Gibson and Daniel Strange, eds., Engaging with Barth: Contemporary Evangelical Critiques (Grand Rapids: Bloomsbury T&T Clark, 2009), 346-81。本文为该书的第12章。承蒙授权翻译转载,特此致谢。——编者注
[2] Cornelius Van Til, Christianity and Barthianism (Phillipsburg: Presbyterian & Reformed, 1962). 在这本书之前,范泰尔在《新现代主义》(The New Modernism)一书中评价了巴特和布龙纳(Brunner)(Phillipsburg: Presbyterian & Reformed, 1946)。
[3] G. C. Berkouwer, The Triumph of Grace in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56).
[4] Charles C. Ryrie, Neo-Orthodoxy (Chicago: Moody, 1956), 62.
[5] 关于巴特对这一点的承认,参见Karl. Barth, Letters: 1961–1968, trans. G. W. Bromiley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1), 101. 有关对此的分析,尤其参见:B. L. McCormack, Karl Barth’s Critically-Realistic Dialectical Theology: Its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1909–1936 (Oxford: Clarendon, 1995)。
[6] 除了巴特的海德堡教理问答注释和一些零散文章之外,他对改革宗信条最为明显的肯定性论述,请参见:K. Barth, The Theology of the Reformed Confessions, 1923, Columbia Series in Reformed Theology, trans. D. L. Guder and J. J. Guder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2002)。
[7] John Webster, Barth (London: Continuum, 2000), 41.
[8] Bernard Ramm, After Fundamentalism: The Future of Evangelical Theology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3), 14.
[9] B. L. McCormack, Karl Barth’s Critically-Realistic Dialectical Theology: Its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1909–1936, 253.
[10] B. L. McCormack, Karl Barth’s Critically-Realistic Dialectical Theology: Its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1909–1936, 146.
[11] 即使在此,应该指出的是,巴特对克尔凯郭尔的欣赏是与他的自由派导师威廉·赫尔曼一样的。
[12] Karl Barth, 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 trans. E. C. Hoskyn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3), 369.
[13] Karl Barth, GD 27.III, cited by D. L. Migliore, “Karl Barth’s First Lectures in Dogmatics: Unterricht in der christlichen Religion”, in Karl Barth, The Göttingen Dogmatics:Instruction in the Christian Religion, vol. 1, trans. G. W. Bromiley, ed. H. Reiffen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1), xxxviii.
[14] K. Barth, The Theology of the Reformed Confessions, 134. 同往常一样,巴特在分析这条轨迹时,他的叙述从圣约神学家的救赎历史方法,转向施莱尔马赫和更正教自由主义的历史化方法(135-40页)。
[15] B. L. McCormack, Karl Barth’s Critically-Realistic Dialectical Theology: Its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1909–1936, 266–72.
[16] B. L. McCormack, Karl Barth’s Critically-Realistic Dialectical Theology: Its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1909–1936, 266–69.
[17] Hans Urs von Balthasar,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 Exposition and Interpretation, trans. E. T. Oakes (San Francisco: Ignatius, 1992), 94.
[18] Hans Urs von Balthasar,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 Exposition and Interpretation, 371.
[19] Karl Barth, The Word of God and the Word of Man, trans. D. Horton (New York: Harpers, 1957), 244.
[20] 例如,见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I/1, 182, 189, 194, 202。我很感激我的学生Brannan Ellis指出了其中的一些参考资料。参见G. Hunsinger, Disruptive Grace: Studies in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2), 312–13。
[21] George Hunsinger, How to Read Karl Barth: The Shape of His The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30–31. 柏寇伟(下文论述)也看到了同样的动力,参见G. C. Berkouwer, The Triumph of Grace in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 trans. H. R. Boer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56)。
[22] Hans Urs von Balthasar,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 Exposition and Interpretation, 25.
[23]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1, 132.
[24]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V/4, 105, 129–30 etc. 该卷为巴特发展和出版但未完成的教义学的片段,标题为《基督徒生活》(The Christian Life)。参见Church Dogmatics IV/3.2, 756, 783, 790, 843–901。
[25] Karl Barth, God and Ration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45, 137–38, 155–56, 185.
[26] P. L. Metzger, The Word of Christ and the World of Culture: Sacred and Secular Through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3), 50。借鉴B. L. McCormack, Karl Barth’s Critically-Realistic Dialectical Theology: Its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1909–1936, 365. 对于麦考马克对巴特的“克尔凯郭尔式”的辩证法和“黑格尔式”的辩证法的有益区分,我谦卑地建议另外一种:sub contrario(以相反的形式)。同路德和克尔凯郭尔一样,巴特强调上帝不仅通过适应我们的软弱的方式(加尔文的强调),而且还以相反的形式来显明自己。我们在威严的荣耀中寻找上帝,然而却只可能在十字架和受苦中找到祂。云格尔(Eberhard Jüngel)可能比巴特更强调这一点,但他似乎受巴特的影响与受到自己的路德宗传统的影响相差无几。例如,云格尔写道:“如果在这段历史中(上帝与人类之间),上帝已经与人类同在,那么就其本身而言,人类肯定已经与上帝同在。”特别是在云格尔那里,唯意志论(voluntarism)是显著的:唯一能够将上帝与创造物区分开来的是祂的自由意志,祂能够成为祂愿意成为的一切(God’s Being Is in Becoming [Edinburgh: T. & T. Clark, 2001], 96, 45-46, 89.)。“从起初开始,耶稣就是得胜者”(94页)。另见韦伯斯特对云格尔的基督论的详细分析:In Word and Church: Essays in Christian Dogmatics (Edinburgh: Continuum, 2001), ch. 5。
[27]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2, 499.
[28]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2, 500.
[29]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2, 500.
[30]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2, 492.
[31]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2, 507.
[32]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1, 132.
[33]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1, 133.
[34]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1, 133.
[35]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1, 133.
[36] G. G. Bolich, Karl Barth and Evangelicalism (Downers Grove: IVP, 1980), 196–97.
[37]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1, 123–24. 参见J. D. Morrison, ‘Barth, Barthians and Evangelicals: Reassessing the Question of the Relation of Holy Scripture and the Word of God’, TrinJ NS 25 (2004), 187-213。
[38]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1, 304.
[39]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2, 509.
[40]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2, 509-10.
[41] Karl Barth, The Word of God and the Word of Man, 65.
[42] Karl Barth, The Word of God and the Word of Man, 65.
[43] Karl Barth, The Word of God and the Word of Man, 66.
[44] Karl Barth, The Word of God and the Word of Man, 72.
[45] Karl Barth, The Word of God and the Word of Man, 90.(着重强调是后加的)
[46] Karl Barth, The Word of God and the Word of Man, 90.
[47]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2, 518.
[48]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2, 520-21.
[49]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2, 522–23.
[50]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2, 525.
[51] 关于这一点,在可以引用的众多次级文献中,最为精辟并得到充分支持的是R. A. Muller, Post-Reformation Reformed Dogmatics: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Reformed Orthodoxy, ca. 1520 to ca. 1725, vol. 2: Holy Scripture, the Cognitive Foundation of Theology, 2nd ed.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03)。
[52]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2, 526.
[53]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2, 527.
[54]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2, 528.
[55]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2, 530.
[56]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2, 530.
[57] John Calvi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trans. F. L. Battles, ed. J. T. McNeill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60), 1.13.1.
[58] John Calvi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1.17.13.
[59] Otto Weber, Foundations of Dogmatics, trans. D. L. Guder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1), vol. 1, 78–181.
[60] 见我的《圣约与末世论:神圣戏剧》(Covenant and Eschatology)一书关于卡尔·亨利的讨论。Michael S. Horton, Covenant and Eschatology: The Divine Drama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2002), 189–91。
[61] David Kelsey, The Uses of Scripture in Recent Theology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75), 209.
[62] Karl Barth, 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 347.
[63] Karl Barth, 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 347.
[64] G. C. Berkouwer, The Triumph of Grace in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 256. 范泰尔在整篇《基督教与巴特主义》中都提出了同样的批评,但柏寇伟的分析更加谨慎和有说服力。根据E. Busch, Karl Barth: His Life from Letters and Autobiographical Texts, trans. J. Bowden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76),巴特说柏寇伟的批评“由于其颇有洞察力的分析和所提出的问题,带给了他非常多需要思考的事”(381页)。
[65] G. C. Berkouwer, The Triumph of Grace in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 255–58.
[66]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I/1, 319–20.
[67] Karl Barth, The Word of God and the Word of Man, 120.
[68] Karl Barth, The Word of God and the Word of Man, 59.
[69] Karl Barth, The Word of God and the Word of Man, 207.
[70] P. L. Metzger, The Word of Christ and the World of Culture: Sacred and Secular Through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 97. 参见 G. W. Bromiley,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 (Edinburgh: T. & T. Clark;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9), 248。
[71] Hans Urs von Balthasar, Unser Auftrag, 85, cited by E. T. Oakes, Pattern of Redemption: The Theology of Hans Urs von Balthasar (New York: Continuum, 1997), 306, n. 10.
[72] B. L. McCormack, Karl Barth’s Critically-Realistic Dialectical Theology: Its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1909–1936, 147.
[73] Karl Barth, 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 36.
[74] Karl Barth, 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 36.
[75] Karl Barth, 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 341.
[76]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V/4. 参见Church Dogmatics IV/3.2, 756, 783, 790, 843–901。
[77]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V/4, 88.(着重强调是后加的)。
[78]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V/4, 105. 参见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V/4, 102。
[79]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V/4, 130.
[80]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V/4, 129–30.
[81] 见D. Allen, “A Tale of Two Roads: Homiletics and Biblical Authority”, JETS 43.3 (2000): 492;参见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1, 127。
[82] G. Hunsinger, Disruptive Grace: Studies in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 135.
[83] G. Hunsinger, Disruptive Grace: Studies in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 275–76.
[84] 见F. LeRon Shults, “A Byzantium to Karl Barth”, TS 57 (1996): 431–46; U. M. Lang, “Anhypostasos-Enhypostasos”, JTS 49.2 (1998): 630。舒尔茨(Shults)指出,这个表述是巴特提出的,而不是源于初代教会或更正教经院哲学。改革宗经院哲学确实肯定了传统共识,而不是他们特有的观点,即只有在逻各斯(Logos)取了人性之后,基督的人性才得以存在。然而,他们并没有将其诉诸“隐藏–显露”的辩证法,并且像加尔文一样,怀疑亚波里拿留式(Apollinarian)的倾向,即低估基督的人性对救赎的重要性。
[85] 乔治·亨辛格在《破坏性的恩典》(Disruptive Grace)中对巴特辩证处理的出色分析,使我对巴特基督论的批评感到自责。由于我们无法同时谈论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所以很容易在某点上听起来是近似幻影论(quasi-docetic),而在另一点上听起来又近似阿里乌主义(quasi-Arian)(以及亚历山大学派和安提阿学派的极端)。只有作为一个整体,尤其是考虑到巴特对迦克墩准则的强烈肯定,我们才能避免从孤立的段落中得出对巴特的片面解释。尽管如此,我仍然确信巴特在基督论上的漂移。他如此强调基督的神性,以至于没有给予基督的人性的救赎性意义以足够的重视。关于此,更多的内容参见我的Lord and Servant: A Covenant Christology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2005), ch. 6。
[86]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II/2, 70.
[87] P. L. Metzger, The Word of Christ and the World of Culture: Sacred and Secular Through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 50, 借鉴 B. L. McCormack, Karl Barth’s Critically-Realistic Dialectical Theology: Its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1909–1936, 365。
[88] Stanley Grenz, Revisioning Evangelical Theology: A Fresh Agenda for the 21st Century (Downers Grove: IVP, 1993). Clark Pinnock,Roger Olson和John Franke(仅举几例),也都遵循了类似的轨迹。
[89] M. S. Horton, “Is Evangelicalism Reformed?”, Christian Scholar’s Review 31.2 (2001), 131–68.该书包括奥尔森(Roger Olson)的回应。
[90] Karl Barth, The Word of God and the Word of Man, 253.
[91] 例如,斯坦利·格伦茨(Stanley Grenz)在《Revisioning Evangelical Theology》一书中建议:“在完成神学任务时,诉诸于圣经和文化当然不是福音派方法所独有的。事实上,或许二十世纪中对这种方法最博学的阐述就是保罗·蒂利希所提出的著名的关联法。”他又将对“卫斯理的神学四边形”(Wesleyan quadrilateral)连同其四种来源(圣经、理性、经验、传统)的日益流行,作为灵性胜过了神学的证据(尤其是普林斯顿神学所定义的后者),参考90–91页。
[92] John Franke, The Character of Theology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05), 103.
[93] Laura Smit, “The Depth Behind Things”, in J. K. A. Smith (ed.), Radical Orthodoxy and the Reformed Tradition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05), 209.
[94] John Franke, The Character of Theology, 103.
[95] John Franke, The Character of Theology, 103.
[96] Stanley Grenz and John Franke, Beyond Foundationalism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2001).
[97] Karl Barth, foreword to Heinrich Heppe’s Reformed Dogmatics: Set out and Illustrated from the Sources, ed, and trans. G. T. Thomson, rev. E. Bizer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50), vi-vii.
[98] Karl Barth, GD, 21.
[99] 1924年1月26日写给布龙纳的信,由B. L. McCormack, Karl Barth’s Critically-Realistic Dialectical Theology: Its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1909–1936, 332引用。
[100] Karl Barth, GD, 18.
[101] Karl Henry, God, Revelation and Authority, 6 vols. (Paternoster: Carlisle, 1999).
[102] G. Hunsinger, Disruptive Grace: Studies in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 338–60;此前发表于T. R. Phillips and D. L. Ockholm (eds.), The Nature of Confession (Downers Grove: IVP, 1996), 134–50。在Disruptive Grace的另一章中,亨辛格引用了巴特的大意:“通过上帝的启示”,我们成为了这一事件的“参与者”(II/1, 49),接受并有份于上帝永恒的自我认识(II/1, 68)。因为“上帝将祂自己赐给我们,使得我们可以在祂自我认识的真理中认识祂(II/1, 53),于是我们分享祂自我认识的真理(II/1, P.51)”。然而,这是“间接的”,因为它通过基督作为媒介(Disruptive Grace, 170–71)。即使承认巴特“隐藏-显现”的辩证法,这些引述似乎也暗示了一种单义性的观点,尽管亨辛格声称巴特更接近于类比视角。我会争辩说,即使在我们与基督的联合中,我们也没有分享上帝的自我认识。这些区分所考虑的不仅是方式(直接/间接),而是其内容本身。这并不是否定基督所传递的是真实的知识,而是说这些知识是,而且永远是类比性的和摹本性的。
[103] G. Hunsinger, Disruptive Grace: Studies in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 340.
[104] G. Hunsinger, Disruptive Grace: Studies in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 340–41.
[105] G. Hunsinger, Disruptive Grace: Studies in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 340–41.
[106] G. Hunsinger, Disruptive Grace: Studies in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 355.
[107] G. Hunsinger, Disruptive Grace: Studies in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 355.
[108] G. Hunsinger, Disruptive Grace: Studies in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 356.
[109] G. Hunsinger, Disruptive Grace: Studies in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 356.
[110] G. Hunsinger, Disruptive Grace: Studies in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 356–57.
[111] G. Hunsinger, Disruptive Grace: Studies in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 356–57.
[112] G. Hunsinger, Disruptive Grace: Studies in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 357–58.
[113] G. Hunsinger, Disruptive Grace: Studies in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 11.
[114] G. Hunsinger, Disruptive Grace: Studies in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 358, 359.
[115] G. Hunsinger, Disruptive Grace: Studies in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 360.
 《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
《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