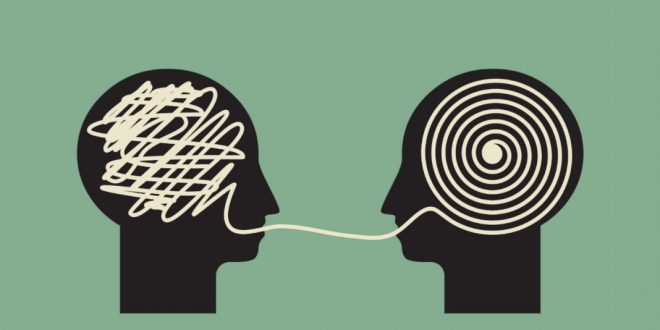文/彭国玮
本文旨参考功能翻译理论的目的论(Skopos Theory),探索汉译圣经的未来方向。第一部分会简介功能理论。第二部分以功能理论回顾马礼逊至《和合本》的汉译圣经历史,继而指出《和合本》出版后汉译圣经发展的一些现象,文末的建议希望可以帮助汉译圣经寻找未来的路向。
功能翻译理论速写
我们先回顾近数十年功能翻译理论的发展,好为下一部分的讨论作预备。奈达(Eugene A. Nida)的《翻译科学探索》[2](1964年)和《翻译理论与实践》[3](1969年出版;与泰伯[Charles R. Taber]合著)两本著作,将翻译的形式对等和动态相符分别开来[4],并提出译者关心的应该是“接收者的回应”,而不是“信息的形式”。[5]因此,翻译的任务就是“要采用译入语最自然和最接近源语的方式,这方式以意义为先,风格为次”。[6]要达到这个目的,奈达提出翻译的三个步骤:开始时要分析源语文本(源文)的文法和语意,然后要将第一步所找出来的元素转化成译入语(目的语),最后就要重新安排目的语的各个元素。[7]后来,奈达在另一本著作《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与德•瓦德[Jan de Waard]合著)改进自己的理论,用“功能相符”取代“动态相符”,[8]又重申翻译其实就是沟通,翻译的内容应该是文本的意思。[9]
奈达的翻译理论对1960年代以后的圣经翻译有重要的影响,这影响不但在联合圣经公会之内,也在联合圣经公会之外。奈达的影响甚至超越圣经翻译的范畴,事实上,奈达的理论也为现代翻译研究奠定基础。[10]
奈达的理论虽有很多可取之处,但有关相符的理论也引出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一个关键的议题是“带有改写文本元素的翻译”(即“相符”)和“带有翻译元素的文本改写”(即“非相符”)之间的分野。[11]这里的问题是,翻译可以进行到什么地步,让翻译可以重构文本,却不致于从翻译踏进改写的范畴。另一个引申出的重要议题是,因为译文不需要重新展现源文的形式,这代表可以有多于一个相符的译法,但我们可以怎样评定这些不同的译法,并且分辨出其中哪一个是最接近源文的译法?莱思(Katharina Reiss)从翻译研究的训练出发,指出要求将源文的作者动机表达给译文读者时,将会有几种情况是不需要相符的:例如在翻译要达到一个与源文不同的目的或功能时,又或当译文针对的读者群与原本文本所面向的读者群不同时,翻译都不一定要相符(可参看诺德[Christiane Nord]对莱思的评价[12];以及莱思的看法[13])。在这些例外的情况下,单单参照源文本身的特征已经不足以评定译文是否适切;翻译的背景也成为评定译文的重要因素。这些议题都迫使我们要进一步发展翻译理论,来进行翻译评鉴和翻译训练。
这些议题令莱思的学生费米尔(Hans J. Vermeer)发展出翻译目的论(skopostheorie / skopos theory),来作为一个普遍的翻译理论。对费米尔来说,译文要达到的目的不一定是源文的写作动机,正如莱思所指出,每一份译文及其与源文的关系,都应该要按着译文的目的来判断;费米尔用了希腊文的“目的”(skopos)一词作一个专门的术语来表达译文目的。[14]诺德因此认为有必要分别“动机”和“功能”:“动机是从发讯者的角度出发,是发讯者希望文本达到的功能”,而“接收者是按着自己的期望、需要、先前的知识和情况,以某一个功能来运用文本”[15]。因为翻译的目的(skopos),是关心译文的功能,所以翻译目的论基本上也属于一种功能翻译论。
对于费米尔、诺德和其他功能翻译理论家来说,好的译文不是如奈达所提出的,一个与源文最相符的译文,最好的译文应该是能够达成它本来要满足的目的的译文。换言之,这里所关注的是社会学的向度(主要是关乎译文的受众),而不是语言学的向度(主要是关乎源文文本)。不过,我们不该说奈达没有考虑社会学的向度,因为他已经说过:
即使回到那个老问题:这是不是一个正确的翻译?也要基于另一个问题来回答:为了谁?要判断译文是否正确,就要基于这译本所面对的大部分受众是否可以正确理解它来评定。[16]
奈达的功能相符和费米尔的目的论的最基本分别,在于考虑翻译的各个因素时,究竟较重要的是与源文相符,还是符合设定受众的目的。
将目的(skopos)放在翻译活动的中心,在翻译实作上便有下述数个意涵。
- 整个翻译应该始于目的的决定。一个特定的翻译任务的目的,是要由开始这个翻译的人,或是支持这翻译计划的人,又或者是由他们共同来订定的,译者通常会透过一个“翻译任务概要”(translation brief)得知这个目的,其中会列明所需要的是哪一类译文形式。[17]一个“翻译任务概要”通常会列明(预期的)文本功能、译文的设定受众,以及(预计)他们接收文本的时间和地点、传递这个文本的媒介、以及制作或接收这文本的动机。[18]源文的角色基本上是提供资讯、[19]或原始资料,译者要运用这些资料来译出一个可以达到其目的的译文。[20]
- 评定这个过程所产生的译文,标准应该是“适切”(adequacy)而不是“相符”。“适切”是指译文在翻译简介的要求下所达到的品质。[21]换言之,一个按着某一特定翻译简介(也就是一特定目的)译出的译文,就另一份翻译简介而言,不一定是适切的。在翻译目的论中,目标决定手段。
- 关于适切的研究令功能理论家注意到不同的沟通方式,以及相应的翻译过程。诺德认为基本上有两类翻译的过程:
第一类是要在译入语文中产生一份文献化的翻译,其中反映的是一位源文化的传讯者透过源文,在源文化的情况下,要对源文化读者所表达的讯息或部分讯息。第二类是在译入语文中产生一份工具化的翻译,让源文化的传讯者可以跟目标文化的读者沟通,这沟通运用源文(或其某一部分)为典范。那就是说,我们可以分辨“文献”和“工具”两类翻译。[22]
诺德认为,在文献化翻译之下有四种不同的翻译形式:逐字对照翻译(interlinear translation)、字面翻译(literal translation)、辞典编纂式的翻译(philological translation)或异国风味式的翻译(exoticizing translation)。她又认为工具化翻译之下可以有三种形式:等功能翻译(equifunctional translation,使目的语读者经验到源文功能)、异功能翻译(heterofunctional translation,使目的语读者经险与源文相似的功能)、相应翻译(homologous translation,在目的语中产生相应于源文的功能)。我们应该将这些形式视为一个光谱上的不同部分,以逐字翻译为一个极端,到相应翻译为另一个极端。在同一个翻译的工作中,也可以同时有不同的形式存在。而译文的目的决定了这翻译究竟是要偏重文献化的取向还是工具化的取向,而译文的目的也会决定哪一个部分要采用哪一种翻译的形式。
最后,功能论者认为,要制作一份适切的译文,译者的忠诚(loyalty)比译文的“忠信”(faithfulness)重要。[23]这是因为“忠信”与目的文化的读者期望不可分割,所以,“忠信”于一群目的语读者,可能代表要忠实地反映源文的形式,但对于另一群目的语读者来说,“忠信”可能是要准确带出作者的意思。[24]在这种情况下,更重要的可能是译者是否忠诚于他们要达成的目的(skopos)(又或是否忠于那些投资该翻译计划的人,以及这目的要服务的群体,因为忠诚关乎人际关系),并且在这个前提下制作出合乎翻译任务概要的作品。如果译者做得到忠诚,了解该翻译之任务目的的读者,就可以在这目的所框定的范围内有信心地运用这译文,而当读者认为自己的期望超出了所设定的目的,他们可能就要使用别的翻译。
中文圣经翻译的目的:从马礼逊到《和合本》[25]
以上有关功能翻译理论的简介应该足以让我们继续讨论。奈达和其他功能理论所面对的情况和议题,其实早在这些理论出现之前已经存在。虽然在中文圣经翻译的历史当中,要到了1979年出版的《现代中文译本》和《当代圣经》才应用了奈达的相符理论(前者是言明的应用,而后者是不言明的应用),但早在十九世纪,当基督教开始将圣经译为中文的时候,有关于译出形式还是内容的讨论,就已经与中文风格的问题一同出现。早期的中文译文所采用的方针和原则可以让我们重构他们的翻译目的,即便翻译目的(skopos)是较后期发展出来的概念。了解这些早期译本的目的,可以让我们明白当时译者的关切,这些关切可以让我们展望汉译圣经的前路。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和米怜(William Milne)在1823年译出的中文圣经,以及马殊曼(Joshua Marshman)和拉撒(Johannes Lassar)在1822年译出的中文圣经,是汉译圣经的开始。从一开始,译者就面对了选择合适的中文风格的议题。当米怜讨论马礼逊翻译新约的中文风格时,曾提到三种文风:以《四书》、《五经》为典范的文雅风格、一种口语化及用于浅白小说《圣谕》的口语风格,以及一个介乎雅俗之间、用于《三国》及《三国演义》的风格。[26]米怜似乎将介乎雅俗之间的风格又再细分为两种,除了《三国》所用较文雅的风格外,还有一种平实的、朱熹《四书集注》的风格。在米怜看来,这两种风格就是马礼逊译本所参照的中文风格。[27]虽然马礼逊没有完全按着这风格来翻译新约,[28]至少在原则上,他们采用中庸风格的决定反映他们希望可以接触较广大的读者,而又希望可以避免用粗俗的语言。[29]
马礼逊指明要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修订马礼逊译本,而新约的修订工作就分别落在麦都思和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身上。[30]麦都思大致上保留了马礼逊介乎雅俗之间的中文风格,但麦都思比马礼逊更注意中西的分别,所以有时会用意译而不作字面的直译。例如在约翰福音1:5,黑暗被译作“居于暗者”,而约翰福音1:23的“以赛亚说”就被译作“古圣人以赛亚预言”。[31]用功能理论的术语来说,这是典型的异功能翻译(heterofunctional translation),运用目的语文化的概念和用语,在目的语的文化达致源文在源文化的相似功能。
这个崭新的进路和其他原因令大英圣书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在1836年否决印刷他的修订。[32]功能理论会认为,这是因为麦都思和大英圣书公会对于译文的沟通方式有不同的理解。麦都思视这修订的任务为制作出一份有工具功能的异功能翻译,中国人虽然不熟悉基督教文化,却可以从自己的文化经验去理解文本。但麦都思的委托人大英圣书公会却很可能期望一份有文献功能的译文,并希望它可以保留源文的形式和内容。结果,麦都思译文当然遭到大英圣书公会否定。
大英圣书公会的否决令麦都思离开旧约的修订小组,留下郭实腊独自完成旧约的修订。[33]郭实腊修订完旧约之后,又重新修订自己和麦都思修改过的新约。旧约的第一版在1838年出版,整体的方向是更忠于原本的文本,也采用了更文雅的文言。[34]但麦都思却指摘郭实腊没有咨询有学识的中国人,所以麦都思仍然觉得这修订并不完备。[35]麦都思指摘郭实腊没有咨询中国人固然有理,但这也反映麦都思自己的异功能翻译取向,这取向在他其后负责的另一个翻译计划——《委办译本》中也表露无遗。
在1843年,成立了一个联合翻译中文圣经的小组,而麦都思就被选为书记。[36]这小组订立了很多翻译的原则,其中一条列明“凡经各差会审核认可刊行的任何中文圣经译本,须完全符合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原文意义;至于中文成语则容许使用,文笔与体裁亦然。”[37]麦都思对这原则的理解可以在《委办译本》的新约(1850年出版)看见,这译本主要由麦都思和他的英国同事译成,而中文的风格则受王韬的影响甚深。[38]《委办译本》的文风较古典,贴近中国学者的风格,希望可以影响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这个译本仍然采用意译多于直译,[39]就好像麦都思修订马礼逊译本时所做的一样。所以,《委办译本》新约的目的,是要为中国的精英分子提供一个异功能翻译,而不是针对较广的读者群。
因着多个原因,这个委办会因麦都思和他的英国同工请辞而分裂,当时他们已经完成了新约,旧约也已经进行至申命记第九章。[40]麦都思和他的英国同工都是伦敦会的传教士,他们按着《委办译本》的新约翻译原则继续旧约的翻译,在1854年由大英圣书公会出版《伦敦会的旧约》,而在1858年也与《委办译本》的新约一同出版。[41]《委办译本》的新约以及《伦敦会的旧约》备受赞誉,文人更是称颂不已[42]。从这看来,麦都思和他的英国同工实在达成了异功能翻译的目的。另一方面,这译本也被批评为较不忠于原文。[43]从功能理论的角度看来,这个批评不一定合理,因为异功能翻译的目的,并不是要重新表达源文的形式和内容。这不是说异功能的翻译无法让目的语的读者得知源文的形式和内容。在此的重点是,在异功能翻译的目的之下,呈现源文的形式和内容应该后于其他异功能目的对译本的要求。不过,这个批评也让我们注意汉译圣经还有很多未能达成的目的,这也是为什么其他在中国的传教士会采用不同翻译原则的原因。
在麦都思和他的同伴离开之后,在委办小组里的美国同僚在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和克陛存(Michael Simpson Culbertson)的带领下,从创世记开始,用新的原则去重译旧约。他们的目的是用“浅白的翻译,叫一般受教育的人都可以看懂”,[44]又要比《委办译本》的新约更忠于原文。[45]从功能理论的角度看来,要界定什么是“忠于原文”,就先要弄清这翻译的目的是文献化或是工具化。一个忠信的文献化翻译通常代表要展现源文本的形式,对不清楚源文化的读者来说,这通常不是容易理解的译文。但工具化的忠信却要求表达意思。从功能理论的角度看来,裨治文和克陛存所采用的是文献化的忠信,所以,我们不难理解,裨治文和克陛存的译本被认为是忠于原文,却不容易读得懂。[46]当然,可读的程度和展现源文本的形式特质也不一定是水火不容。正如高德(J. T. Goddard)所译、罗尔梯(Edward Clemens Lord)所修订的浸礼宗译本所表明,美丽的语文和忠信的要求是可以并存的。但若忠信的定义是要完全展现原文,而不考虑目的语的句法结构要求的话,那就难以得出流畅的译文的,这正是胡德迈(Thomas Hall Hudson)1867年的新约译本所显出的困难。[47]
当传教士在1860年代可以进入中国的内陆、北京以及天津后,他们才开始感受到官话(译按:即现今称为国语或普通话的前身)在汉译圣经事业上的潜质。[48]传教士发现用官话所译成的圣经,可以接触大多数说官话的文盲,当有人读出官话圣经译本时,这些民众都能够明白。[49]参与《委办译本》的英国和美国译者都将新约译成官话。[50]最早的译本包括由包尔腾(John Shaw Burdon)、施约瑟(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白汉理(Henry Blodget)、艾约瑟(Joseph Edkins)、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译成的《北京官话译本》以及施约瑟所译的官话译本旧约(1874/75年)。这些官话译本的对象是中国大众,而不像从马礼逊译本到《委办译本》所针对的文人阶级。
因为中国的南部有很多不同的方言,所以南方人并不是太懂官话,有些传教士就希望用一种介乎《委办译本》和官话之间的中文风格来译经。这个议题首先在1877年被提出,而杨格非(Griffith John)1885年的新约文言译本就是第一个较浅文言的新约译本。[51]传教士对于较浅文言(或称“浅文理”)的定义有不同的理解,但不论定义是什么,他们使用浅文言时都有清晰的目标,那就是要用一种不单只文人可以明白的风格,这风格也需要穿越官话和方言之间的隔阂。[52]他们期望浅文言可以让大部分中国人明白圣经。杨格非既希望为大部分的中国人译圣经,在译经的时候就用了非字面的译法,对他来说,一个完全采用字面译法的译本“不论对非基督徒还是基督徒都没有价值。对于前者那译本只是一个笑柄,而对于后者那就是一块绊脚石”。[53]功能理论会将杨格非的进路界定为异功能的工具化翻译,尤思德正确地指出:这个进路与《委办译本》和《北京官话译本》所采用的一样。[54]
从1860年代至1880年代的汉译圣经发展中,官话和浅文言这两种风格明显在互相竞争。有些《北京官话译本》的译者在完成官话译本后,就又出版了浅文言的版本(例如包尔腾和白汉理在1884年出版的《浅文理新约》和施约瑟的《浅文理译本》[1899,1906,1910年版])。在另一方面,杨格非又基于1889年出版的《浅文理译本》而出版《官话新约译本》。[55]就是在这种氛围之下,传教士在1890年召开了大会,讨论联合译经的方向。这个大会决定了联合的译经将包括一个浅文言的译本、一个官话的译本,而因为英国的传教士和大英圣经公会对《委办译本》的推崇,又加入了一个以《委办译本》为基础的深文言译本。[56]
联合译本有十八条翻译原则,[57]其中表明新的译本要保留前译本的优点,例如用词的一致、中文的自然可读风格,同时又要比《委办译本》更为直译。被认为三个译本中最重要的《浅文理(浅文言)译本》,最终却是生硬临摹希腊文本的译文,结果,对忠信的追求颠覆了《浅文理译本》的原意,这译本原本是要产生让不太熟悉文言的群体都可以听得懂的译文。[58]功能理论会认为,浅文理的译者有一个关乎忠诚的问题,这问题最终令译本失败。深文理(即深文言)联合译本的新约委员会中有两个成员湛约翰(John Chalmers)和韶泼(Martin Schaub),他们都采用了浅文理联合译本的进路,他们的翻译原则与其他的委员分别太大,最终令他们要自费在1897年出版译本,他们这个译本希望可以改善《委办译本》被认为最不足的地方,也就是不忠于原文。[59]其他的委员却没有依循湛约翰和韶泼的路线。在湛约翰于1899年去世后,委员会重组,并且在1907年出版深文理的联合译本的新约部分,这个译本并没有完全直译希腊文,反而更着重译文的风格是否可读。[60]官话的联合译本新约也面对重重困难,但最后在1907年完成的译文被译者视为“尤其直译原文、忠于原文”,但也同时“在某程度上牺牲了文风的流畅程度”。[61]
在1907年的传教士大会上,决定了结合两个文言版本,令联合译本之下只有一个官话和一个文言的版本。[62]1919年出版的《文理和合本》结合了修订后的深文理联合新约译本,以及按着新约的翻译原则译出的旧约。[63]《官话和合本》也在1919年出版,新约经大幅度的修订,运用比1907年稍为文雅的语言。[64]虽然经过修订,也改变了语文的水平,1919年的版本仍是承袭了1907年新约译本的传统,用了浅白地道的官话来表现源文本的形式,令所有人都可以读得懂。[65]
从以上的简单回顾,我们可以看出,译者要考虑的主要问题,在于读者对象是谁,以及要为读者做出多大调适这两方面。这两个问题反映在不同中文风格的讨论,也反映在强调要译出意思而不是译出语文形式的讨论,后者出现在麦都思几个译经的计划(修订马礼逊新约、《委办译本》的新约部分、伦敦会的旧约翻译)、《北京官话译本》、施约瑟的官话旧约、杨格非的两个版本,甚至出现在1919年出版的文理和官话《和合本》。这异功能的工具化翻译进路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因为当时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不熟悉基督教,犹太和基督教的文化是中国人全然陌生的文化,这些版本受读者欢迎的程度也反映这个进路是有其价值的。
不过,有些译者不满意这个翻译的目的(skopos),并且采用了另一个目的,那就是为读者提供一个可以反映源文形式特色的译本。这个目的之下出现的译本包括裨治文和克陛存的译本、胡德迈的浸礼宗版本、和合译本的浅文理新约。因着当时的历史背景,这些译本得不到支持,但这个目的,却在《和合本》的文理和官话版本出现之后成为汉译圣经的一大关注。
未来汉译圣经的目的:一些观察
当我们想到汉译圣经的未来时,我们会想到什么?我们可能要先考虑早期译者面对过的议题,有些议题我们今日仍是要面对,有些却已成明日黄花。我们也需要想想,是否有一些新出现的需要,是在以往没有出现过的。
功能学派认为翻译是一个跨文化的沟通活动,[66]所以,时间、地域和文化的改变会影响翻译的方式。《和合本》出版的同年发生五四运动,这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紧扣(1915至1923年或1917至1921年)。在这场运动中,官话(即后来的国语或普通话)成为现代中文的书写语。新文化运动为中文带来不可逆转的改变,这改变到今天仍在影响我们。这个改变也反映在《和合本》两个版本的销量之上:《和合本》出版后十年,官话的新约出售了超过一百万本,印刷了五十万本的官话圣经全书。在1939年,也就是《和合本》出版后二十年,已经再没有印刷文理版本。[67]自此以后,国语成为现代中文的唯一书写语,传教士在十九世纪一直挣扎的中文风格问题已经不是汉译圣经要面对的难题。
这不是说有关译本对象和为对象做出多少调适都不再是译者要面对的问题。即使书写语的形式已经确定下来,仍有很多不同的读者群,他们的不同期望仍有待满足。因为书写语已经一致了,这个问题就要用风格以外的方式来理解。从功能理论的角度,不同的读者群对译文的目的有不同的期待,要有效地了解译文的功能,就要好好了解译文对象以及他们接收译文时身处的时间、地域和文化。这是为什么翻译任务概要在指出译文的功能之后,要描述译文对象以及他们接收译文时身处的时间、地域和文化。[68]有关于未来的汉译圣经,我们须要回答以下的问题:
现在和可见的将来有多少个不同的读者群需要服务?我们要分开知识分子和普罗大众吗?基督徒和教会外群众是不是两个群体?这两个群体可否用同一个方式来服务?在基督徒的群体之内,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是两群人吗?合一的翻译方向是否可以满足两者和教外人的需要?我们是否需要在汉译圣经中考虑东正教的读者?
这些问题不一定有特定的答案。但这些问题却可以让译者和支持翻译计划的人弄清某一个翻译计划针对的读者范围,也可以发掘出可能出现的读者群。当我们找出译文的对象后,就要进一步回答以下的问题:
我们预期达到的功能是什么?是偏向工具化的,还是文献化的?如果是工具化的话,在翻译源文时是否容许或是否预期会运用目的语的文化?例如,是否要像《官话和合本》所做的那样,用中国或现代的度量衡和钱币系统来表达古时的单位?又或者,中国古诗的形式是否可以用来翻译诗篇,像湛约翰用楚辞的形式来翻译诗篇二十三篇,[69]或如吴经熊的《圣咏译义初稿》(1946年)那样?[70]当原文用男性来代表所有人的时候,译文是否要用可以同时表达男女的语言?[71]如果是文献化的翻译,译文要反映源文化多少的语文形式和特色?可以用多不自然的中文词句?又可不可以在翻译时发明新的中文用词?
我们当然还可以继续问下去,但以上这些问题的答案却可以帮助我们规划翻译任务概要,我们也可以用这任务概要来评定译文是否适切。
《官话和合本》已经是一个受到认同的传统,不论是《和合本》、对《和合本》的修订,还是在《和合本》基础之上的新的译本,都会继续服务华人教会。《和合本》倾向工具化的翻译,不单可以用于基督教的宣教,也可以服务不熟悉圣经但却对其内容有兴趣的群体。这工具化的功能当然不会完全由《和合本》及其传统来达成,尤其自1919年迄今中文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也有可能在《和合本》传统以外产生其他形式的工具化译本。《现代中文译本》(1979年,1995年修订版)和《当代圣经》(1979年)是两个倾向工具功能的翻译,它们希望可以接触更广大的读者,而不是单单跟随《和合本》的传统。
另一方面,自从《官话和合本》出版之后,一直有声音要求有更忠于原文的译本。很多《和合本》之后出现的中文译本,特别是那些由中国人所译的译本,都希望重现源文本的形式和特色。赛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曾任《官话和合本》旧约的委员,但觉得这个译本的语文不够地道,对原文也不够忠实,所以联同他的助手朱宝惠重译新约,并且在1929年出版了自己的译本。[72]赛兆祥去世后,朱宝惠继续修改他们一同翻译的译文,并且重新译出了新约,这《重译新约全书》(1936年)直译经文,并且希望采用一致的用词。[73]吕振中也采用了直译的方式,在1946年出版了新约译本,新约的修订版在1952年出版,而《旧新约全书》就在1970年出版。近年出版的几个中文译本,都用了“忠于原文”或类似的用语来解释它们的翻译原则。[74]对“忠于原文”的执着反映《官话和合本》的异功能翻译进路未能满足一些读者的要求。华人教会在《官话和合本》的帮助下发展,但也同时需要有译本可以让华人进行研究和深入的学习。这个需要却超越了《官话和合本》的目的,只可以由一些文献化的翻译来达成。严复的翻译理论“信达雅”影响深远,这也可能是圣经译者追求的“忠信”[75]的理由,因为按严复的说法,一个好的翻译的首要条件就是忠于原文。
严复理论的问题却在于“信”该如何在实作中实现。若没有清晰的指引,就不太可能对这个翻译的要求有一致的应用。例如,朱宝惠翻译路加福音3:24-37[76]时,尽量保留了希腊文的形式,这也可能是《新译本》在翻译这段经文所根据的范本。然而,如果“信”是保留原文本的形式,那朱宝惠译本和《新译本》都将提阿非罗的名字放在路加福音1:1,《官话和合本》也是这样,但在希腊文的文本,这名字却是要到1:3的最后才出现。有趣的是,《吕振中译本》的确将提阿非罗的名字放在1:3的最后,这符合希腊文的形式,但到了路加福音3:24-37,吕振中却跟随《官话和合本》,没有像朱宝惠的翻译那样保留了原文的形式。在约翰一书1:5,《官话和合本》[77]倒转了希腊文子句的次序,《吕振中译本》和《新译本》都跟随《官话和合本》,而没有尝试保留原本希腊文的子句次序。相对于此,《现代中文译本》本来不是一个直译的译本,在此却忠实地保留了希腊文子句的结构。[78]如此一来,这叫不懂得希腊文的读者怎样去判断哪一个译本比其他译本更能够保留原文的形式?若不能够一致地应用翻译的原则和指引,不懂得源语文的读者就很难透过译文去重构源文的形式。
也许按着译本的目的(skopos)先来确定翻译的形式,[79]方能解决上述的议题。诺德列出了文献化翻译的四种模式:逐字对照翻译(interlinear translation)、字面翻译(literal translation)、辞典编纂式的翻译(philological translation)或异国风味式的翻译(exoticizing translation)。[80]这些形式的可读程度不同,反映源文语文特色的程度也不同。如上所述,这四种模式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在同一个光谱上不同的可能。一个翻译若有清楚的目的,就可以帮助译者决定这译文属于光谱上的哪一点。这就可以发展出一套的指引,令译出来的译文可以一致地处理其反映原文本形式的取向。
中文有一些独特的句法特性,要在充分考虑这些特性的前提下译出一致的汉译圣经,以上所提的就更加重要。不论在希伯来文还是希腊文(特别是在后者),修饰语(副词与形容词)可以出现在被修饰的动词或名词的前面或后面,关系子句也可以出现在被修饰的对象之后。中文的修饰语一定要在所修饰的对象之前,中文也没有关系子句。因此,一个译本愈想反映原文的形式,就愈有可能偏离自然的中文表达方式;特别是处理复杂的关系子句时,根本就不可能用有意义的中文来反映原文本的形式。所以,若没有解释一个译本是怎样“忠于原文”,却声称该译本“忠于原文”,就可能会误导了读者。[81]若能够好好定下译文的目的(skopos),又有翻译任务概要,就可以厘清这问题。
从功能理论看来,文献化的翻译目的是可以用不同方式来达成的。功能理论作为普遍性的翻译理论,会视翻译为一种“翻译性的互动过程”,让不同文化群体可以互相沟通。[82]这沟通可以藉着文本(狭义的“翻译”),也可以透过某种“翻译活动”达成,例如在跨文化的沟通中提供文化的信息或忠告。[83]若用于圣经翻译,译出原文的形式和内容只不过是达到文献目的的一种方式。这目的也可以藉一个工具化的“翻译活动”来达致,例如提供语文、历史、地理和文化资讯的附注等。换言之,文献化的目的可以藉研读版的圣经来达致。若要彼此沟通的两个文化之间有极不相同的语言系统和文化,好像中国和古代希伯来文化之间,又或者像中国和古代希罗文化之间,提供附注的“翻译活动”这个进路的好处,是可以提供很多语文和背景的信息,却不受狭义的翻译所容许的文本的限制,此时译文可以采用更自然、更通顺的翻译方式,因为译文有附注的解说,译文本身不需要承载反映原文形式的功能。
结语:几点建议以供思考
功能进路的起始点,是承认没有一个译本可以达致跨文化沟通要求的所有功能。若有一个译文声称可以满足受众所期待的所有功能,这译文很可能只可以有效地满足某些功能,又或者,有时连一个功能也不能有效地满足。这就是功能理论学者为什么这样看重翻译目的的订定,因为翻译的目的可以指出一个译文预备达成的功能,这样就让译文更有可能达成这些功能。因此,若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可以看到一系列以不同目的来主导的中文翻译或翻译活动的话,华人和华人教会就会得到莫大的裨益。
《官话和合本》的传统在华人新教的教会已有九十年的历史,这个传统相信会、也应该会继续下去。除了在这个传统之下的修订和重译,我们还可以考虑在《和合本》传统的经文旁加上研读的注记。这些研读本的圣经可以用文献化翻译为取向(提供语文、历史、文化的讯息),也可以是用工具化翻译为取向(提供神学、诠释、甚至是应用的讯息)。
在过去数十年中,中文急遽转变,圣经研究也有很大的进展,这让《官话和合本》难以继续实现其本来的目的(skopos):也就是将圣经的讯息传递给最广的华人受众。我们需要其他工具化的中文译本来达成这个目的。这些译本可以用来服务一般教育程度而又不熟悉基督教的读者,[84]也可以聚焦在译本中文风格的文学质量,[85]又或者特别为儿童和年轻人而翻译。
至于文献化的翻译,我们期望有译本可以比《吕振中译本》更能够重现原本的形式。因《和合本》有其工具化的倾向,文献化翻译的译者要容许自己不受《和合本》的传统束缚。这些文献化的翻译目标是供学者研究之用,即使不一定考虑东正教的传统,也可能要考虑结合基督新教和罗马天主教的传统。
以上的意见可能会令人担忧,多样化的译本会不会叫读者感到混淆。功能理论的角度认为,如果每个翻译都有清晰的目的,又可以有效地实现其目的,读者便不会感到混淆。只有在各个译本的翻译目的不清,又或者在某些译本声称可以达到一些它们不可能达到的目的时,读者才会感到无所适从。这篇文章的写作目的,就是希望这类的混淆不会出现。
参考文献
(除注释所列的文章、书刊之外,本文亦参考了以下书列)
《中文标准译本圣经•新约》(Nashville, TN: Holman Bible Outreach International,2008)。
《和合本修订版》(香港:香港圣经公会,2006)。
《现代中文译本》(香港:香港圣经公会,1979)。
《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台北:中华民国圣经公会,1995)。
《当代圣经》(香港:国际圣经协会,1993年第四修订版)。
《新译本》(香港:天道书楼,1992,1999,2001)。
朱宝惠,《重译新约全书》(香港:拾珍出版社,1936,1993年重印)。
吕振中,《吕译新约初稿》(北京:燕京大学,1946)。
吕振中,《新约新译修稿》(香港:香港圣经公会,1952)。
吕振中,《旧新约圣经》(香港:香港圣经公会,1970)。
吴经熊,《圣咏译义初稿》(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李炽昌和李天纲,〈关于严复翻译的《马可福音》〉,《中华文史论丛》64(2000):51-75。
冯象,《摩西五经》(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
冯象,《智慧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
严复,《马可所传福音:第一章至第四章》(上海:大英圣书公会,1908)。
作者简介
彭国玮,国立台湾大学学士学位,中华福音神学院道学硕士,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哲学博士。1997迄今任联合圣经公会亚太区圣经翻译顾问。
[1] 彭国玮,〈从功能理论进路探索汉译圣经前路〉,于《自上帝说汉语以来——〈和合本〉圣经九十年》,谢品然和曾庆豹合编,圣经与公共生活丛书,译经与释经系列(香港:研道社,2010),171-90。此文原以英文发表,由李隽教授译为中文,并经作者审定,收入《自上帝说汉语以来》。承蒙授权转载,特此致谢。——编者注
[2] Eugene A. Nida,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Leiden: E. J. Brill, 1964).
[3] Eugene A. Nida and Charles R. Tab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Leiden: E. J. Brill, 1969).
[4] Nida and Tab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12.
[5] Nida and Tab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1.
[6] Nida and Tab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12.
[7] Nida and Tab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33.
[8] Jan de Waard and Eugene A. Nida,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Functional Equivalence in Bible Translating (Nashville, TN: Thomas Nelson Publishers, 1986), vii.
[9] Jan de Waard and Eugene A. Nida,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9ff, 60ff; compare with Nida,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30ff, 120ff.
[10] Edwin Gentzler,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46.
[11] Christiane Nord,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Manchester: St. Jerome, 1997), 8.
[12] Nord,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9.
[13] Katharina Reiss, “Type, Kind and Individuality of Text: Decision Making in Translation” (1971), translated by Susan Kitron, in Lawrence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4), 168-69.
[14] Hans J. Vermeer, “Skopos and Commission in Translational Action” (1989), translated by Andrew Chesterman, in Lawrence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4), 227-29.
[15] Nord,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28.
[16] Nida and Tab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1.
[17] Nord,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20-21.
[18] Nord,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60.
[19] 事实上,功能理论视一个文本——不论是源文或是译文——的功能都是资讯的提供。
[20] Nord,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37.
[21] Nord,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35.
[22] Nord,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47.
[23] Nord,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123ff.
[24] Nord,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124-125.
[25] 这里的讨论是基于尤思德(Jost Oliver Zetzsche)有关中文圣经翻译的历史研究。Jost Oliver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the Union Version or The Culmin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ary Bible Translation in China,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XLV (Nottotal: Stcylor Verlug, 1999).
[26] 尤思德引用了米怜。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33.
[27]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35.参见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33-34。
[28]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35-37.
[29]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34.
[30]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59-62.
[31]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64.
[32]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65.
[33]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67-68.
[34]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68-70.
[35]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70.
[36]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77-80.
[37]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79.
[38]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91-92.
[39] 尤思德有举例说明。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95.
[40]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98.
[41]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97-100, 102.
[42] 赵维本,《译经溯源:现代五大中文圣经翻译史》(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1993 ),21。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102-103.
[43] 赵维本,《译经溯源》,21。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103.
[44]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99.
[45] 尤思德有举例说明。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106.
[46]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105-107.
[47]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122 n55.
[48]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139-141.
[49]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140.
[50]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141.
[51]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161.
[52]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162.
[53]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165.
[54]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167.
[55]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170-183.
[56]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194-195.
[57]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225-226.
[58]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227, 232-235.
[59]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243-247.
[60] 参尤思德引用惠志道(John Wherry)的解释。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252-253.
[61] 参尤思徳引用狄考文(Calvin W. Mateer)的解释。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252-253.
[62]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285ff.
[63]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297ff.
[64]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322-329.
[65]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324-325.
[66] Nord,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22-25.
[67]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331.
[68] Nord,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50.
[69]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213 n82.
[70] 这些译本是很好的例子,来说明诺德所提出的相应翻译(homologous translation)。
[71] 这些问题不是关乎工具化翻译的所有问题。译者要不断寻索跨文化沟通过程中出现的其他问题。
[72]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308-311.
[73]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340-343.
[74] 例如,可以参考《新译本》(1992年)的前言,《和合本修订版》(2006年)的前言,以及《中文标准译本》(2008年)的翻译原则。
[75] 这理论在严复翻译赫胥黎(Thomas H. Huxley)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的引言提出。对于这理论的研究可见于沈苏儒,《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0)。
[76] “由希里以上,就是马塔。利未。麦基……马勒列。该南。以挪士。”
[77] “上帝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这就是我们从他那里听见,现在传给你们的信息。”
[78] “现在我们要从上帝的儿子所听到的信息传给你们:上帝是光,他完全没有黑暗。”
[79] Nord,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48, 51.
[80] Nord,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47-50.
[81] 这是应用严复理论的一个主要问题。从严复翻译马可福音一至四章的情形看来,他所说的“信”不大可能代表重现源文本的形式,也不大可能是逐字的翻译。例如,在马可福音4:3,严复将撒种的人(sower)译作“农人”,而在马可福音4:7,原文直译为“有些跌在荆棘里,荆棘长起来,就窒息了 它”,严复却译作“又或入荆棘充塞,夺其土膏”。
[82] Nord,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16-17.
[83] Nord,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17.
[84] 例如《现代中文译本》和《当代圣经》。
[85] 例如冯象的《摩西五经》和《智慧书》。
 《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
《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