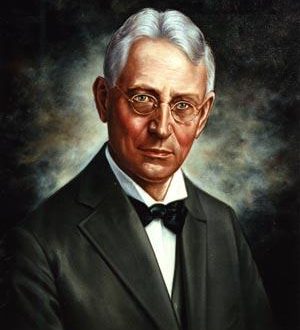文/魏司坚(Geerhardus Vos) 译/凯若思 校/诚之
一、盟约教义史略
1、盟约思想与改革宗神学
当前的普遍共识是,盟约教义是改革宗特有的教义。它与改革宗神学天生一对儿,某种意义上,它也只能和改革宗神学一对儿。诚然,在十七世纪将近尾声时,好几位路德宗神学家也采用了这个教义,但这显然是模仿来的,在真正的路德宗框架内找不到这个教义。另一方面,在改革宗神学家那里,它获得了最为长足的发展,强有力地主导了神学思想工作,否则后者大有可能走向截然不同的方向。
最后一点导致一种看法,认为盟约教义是某种新事物,它虽然确实成长于改革宗神学土壤,却首先出现在柯塞尤斯(Cocceius)及其学派那里。因此可以说,柯塞尤斯主义(Cocceianism)与盟约神学是一回事。假如这是在说,柯塞尤斯是用盟约观念主导其神学体系的第一人,那这话还有几分道理。但是就算如此也不全对。荷兰的克洛彭博格(Cloppenburg)和格里乌斯·斯内卡努斯(Gellius Snecanus)此前已经提出了一种盟约神学,德国的奥利维亚努斯(Olevianus)也是。柯塞尤斯的创新并不在于盟约神学,而是基于盟约理念,为救赎的展开施行所得出的历史性结论。此结论一出,反对柯塞尤斯主义的争议就开始了。
若不单看盟约神学,而是关注盟约观念本身,那么我们还可以回溯到更早。很多改革宗神学家在他们的体系中都有关于盟约(covenant)或遗命(testaments)的论题。提尔卡修斯(Trelcatius)父子、尤尼乌斯(Junius)、葛马乌斯(Gomarus)等人都在此意义上教导过盟约。对他们来说,盟约理念更多是从属性的,所以他们不能被称为——就这个词后来的含义而言——盟约主义者(federalists)。
然而,特别是在德国,盟约教义找到了发展的肥沃土壤。不仅海德堡神学家们,还有其他一些人也与之有特殊关联。这导致有人认为,我们其实是在面对一种地地道道的德国现象。盟约理念被看做是一种原汁原味的趋势(这种趋势被一些人称为“德国改革主义学派”)的特色之一。它被认为并非源自瑞士宗教改革和加尔文主义,而是传承自梅兰希顿在Augustana(《奥斯堡信条》及其《辩护》)中所表述的老日耳曼更正主义(old German Protestantism)。与其说是梅兰希顿后来改变了立场或离开了最初的原则,不如说是后来的路德宗神学背叛了原初的纯正信仰。德国的改革宗传统从变质的路德宗手中拯救了原本的更正教真理。这样一来,盟约教义就该归属于德国更正教而非改革宗。或者说,我们不应在日内瓦寻找真正的改革宗立场,而应该在德国人那里。梅兰希顿而非加尔文,才是真正的领头人。
海珀(Heppe)是这种引人瞩目的历史性解释的推崇者之一,也曾极力为此辩护。若真如此,盟约观念就得被当作入侵改革宗领域的怪异想法而被另眼看待。无论在神人合作的土壤(synergistic soil)里生长的是什么,都不可能结出任何健康的改革宗果实。但几乎不言而喻,这种看法完全站不住脚。海珀本人后来也部分地收回了他的说法。在他的《改革宗教会敬虔主义与神秘主义史》(Geschichte des Pietismus und der Mystik in der Reformirten Kirche, 1879)中,他承认盟约神学源自瑞士而非梅兰希顿,并非兴起于德国,而是自其南边蔓延而来。与其说所谓德国改革宗学派的残余势力只是后来被加尔文主义大潮吞没了,不如说它在非常早期就在德国形成了自己的温床,且以自己的新潮流淹没了自己的阵地。
在瑞士,改教家与重洗派有直接冲突。单是这种外部环境就可能导致他们欣赏盟约理念。在为婴儿洗做辩护时,他们援引旧约,并将对圣礼的盟约理解应用在新的时代,慈运理在1525年就是这样做的。自1534年起,由雷奥·尤达(Leo Judae)出版的多种教理问答,内容强烈地受到盟约理念的影响。布林格的《神学布道五十篇》(Decades)于1549-1551年问世,德文译本改名为《家庭读本》(The Housebook)出版于1558年。这本著作完全以盟约理念为架构。
加尔文也时常提及盟约。但他的神学乃建基于三一论,因此盟约概念无法在他的体系中成为主导原则。他是那些将盟约作为独立要点而赋予其从属地位的改革宗神学家的先驱。即使是他最有可能展开阐述盟约理念的《日内瓦要理问答》(Geneva Catechism)也绕过了它。与此同时,苏黎世的神学家们则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盟约神学(federal theology)的先驱,对他们而言,盟约成了基督徒生活实践的主导理念。
著名的海德堡神学家,奥利维亚努斯和乌尔辛努斯(Ursinus)二人都与苏黎世神学家关系密切。奥利维亚努斯曾在苏黎世待过一段时间,乌尔辛努斯则去过两次。因此显然,盟约观念对他们的影响应该归功于这种联系。乌尔辛努斯在他的《大要理问答》中应用了盟约观念。奥利维亚努斯讨论盟约的著作有两本,即《使徒标记阐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Apostolic Symbol)和《神与选民之间恩典之约的本质》(The Substance of the Covenant of Grace between God and the Elect),分别出版于1576和1585年。
从那时起,盟约主义就不曾从改革宗体系中退出。它在瑞士的穆斯库鲁斯(Musculus, 《教义要点》[Loci Communes], 1599)、珀拉努斯(Polanus,《系统论述》[Syntagma], 1609)和沃勒比乌斯(Wollebius,《信仰纲要》[Compendium], 1625);匈牙利的赛格丁(Szegedin, 1585);德国的皮瑞乌斯(Pierius, 1595)、索尼乌斯(Sohnius,《神学方法》[Methodus Theologiae])、艾格琳(Eglin, 1609)和玛尔提努斯(Martinius)的著作中都可见到。而在荷兰,我们也同样可以在尤尼乌斯、葛马乌斯、提尔卡修斯(Trelcatius)父子以及奈尔得努斯(Nerdenus)那里见到盟约主义的主要观点,直至最终,克洛彭博格详尽的体系出现,在其中,盟约理念和严谨的加尔文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在他之后就是柯塞尤斯。他们之后的盟约神学家(covenant theologians)的名字就家喻户晓了。
2、工作之约与改革宗神学
这个概览足以说明,古老的作品如何能显明出改革宗神学中的盟约教义。但有人也许会说,这只适用于恩典之约(covenant of grace)。这些历史资料不能证明工作之约(covenant of works;或译为“行为之约”)也属于古老的改革宗学派。这种看法一再被人提出。十七世纪下半叶,乌拉克(Vlak)和贝克尔(Bekker)公开反对工作之约,理由是这是他们那个时代的新发明,在前辈改革宗神学家那里见不到。这是在假设鲁贝尔图斯(Lubbertus)、马可夫斯基(Makkowski)以及克洛彭博格是其最早的推介者。这就好像柯塞尤斯偶尔被视为一般意义上的盟约观念发现者一样,有些人也想宣称,工作之约的教义是紧接着柯塞尤斯之后的时期被设想出来的。如果这意味着,这个教义早先并没有在每一个细节上都被详尽挖掘,也没有如稍后那样被全然清晰地呈现出来,那么它还有几分道理。但任何人只要有历史意识,可以将思想的最初萌芽和成熟发展区分开来,不坚持某种教义从一开始就是成熟的,都能毫无困难地将工作之约视为古老的改革宗教义。乌尔辛努斯的《大要理问答》中就已经有诸如这样的提问:“神的律法教导你什么?”回答是:“神在创造时与人立的是哪一类的盟约,以及人应当如何守约。”同样地,奥利维亚努斯谈到和恩典之约作对比的律法之约、自然之约、创造之约。确实,有时他是在说摩西之约的颁布,但在其他地方说到的工作之约,再清楚不过应当回到堕落之前去寻找。
只有在两点上,早期的工作之约教义被其后的发展所取代。第一点是代表性原则(representation principle)。亚当所有的后代继承了亚当的罪咎,终极原因是他们天生就在其先祖的身内,这种早期的根源论还继续被人持守。此约是和亚当立的,既然所有人都在他里面,这约也就是与所有人立的。后期的理论最终没有(因此并非完全)诉诸自然律,而是诉诸司法性的观念。第二,早期教义未能始终清楚表达的是:工作之约如何与人作为受造物在神面前的天然关系区分开来。后期对这两者则区分得更为清晰。因此,若有人主张工作之约的新颖性,意思是这两点后来变得更为清晰,我们可以同意他。但这不是该教义的全部内容。它的核心位于更深处,而且很早就有了。眼下我们盼望能看到这个核心与改革宗原则有何等密切的关联。不仅如此,我们还必须从中得出一个重要的限制。最早的改革宗神学里有一件事情可以证明,该教义从一开始就是基于承认代表性原则,然后据此线索发展的,那就是灵魂创造说(creationism)。所有人都在亚当身内的观念,并未误导改革宗神学用遗传说(traducianism)来取代创造说。然而,如果改革宗神学确曾彻底严肃地认为,所有人天生就在亚当身内是代代相传的罪咎的终极基础,那自然就会得出遗传说的结论。天然关系是代代相传之罪咎的唯一基础,和灵魂遗传说是密不可分的。改革宗神学家们排除万难,坚持灵魂由神所造,这个事实表明他们怀疑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并本能地转向一个有利于后来原罪教义得以发展的方向。
3、盟约教义在英语世界的发展
盟约教义在英语神学中的发展值得特别关注。它表明盟约主义确实是普遍现象,任何以改革宗原则建构神学之处都会出现盟约主义。在这方面,人们曾经泛泛地认为,不列颠神学家只是在追随荷兰的同道。更深入的研究很快就表明,他们不是在模仿,而是有自己独立的发展。米特切尔(Mitchell)在其著作《威斯敏斯特大会》(The Westminster Assembly, Baird Lecture, 1882)的377页说:“至于有些人宣称源自荷兰的盟约教义,经过仔细查考,我认为我现在有资格说,这个信条所教导的,本质上无不是苏格兰的罗洛克(Rollock)与贺威(Howie),英格兰的卡尔莱特(Cartwright)、普列斯敦(Preston)、帕金斯(Perkins)、埃姆斯(Ames)和巴尔(Ball)在他的两个要理问答中早就教导过的。”事实确实如此。《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是第一个这样的改革宗信条:它不仅是旁敲侧击地引入盟约的教义而已,而且更将其置于显著位置,并且几乎渗透在每一个要点中。大会从1643年即已召开,而柯塞尤斯的《盟约与遗命教义大全》(Summa doctrinae de foedere et testamento)直到1648年才问世,就在那年,《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已经完成并出版。因此显然,威斯敏斯特神学家并未受到任何外国势力的影响,而不过是将他们自己国家中逐渐发展成熟的成果做出总结而已。要追溯这个进程,毫无疑问要再次从布林格开始说起。在玛丽女王统治期间,很多传道人和学者逃到苏黎世。布林格与他们保持了活泼的沟通。前面提到的《五十篇》,在1577年被译成英文,随后又再版多次。当然,这本书的拉丁文版本,其影响就更早了。就我们所知,奥利维亚努斯的《使徒标记阐释》(Expositio Symboli Apostolici)的一个英文译本,直到1618年才由约翰·菲尔德(John Fielde)完成。当然,奥利维亚努斯的这本书与其他著作已经以拉丁文被传阅,这个推测很合理。在此,正如在其他地方,他们在吸引众人注意到盟约观念上做出了贡献。
罗伯特·罗洛克(Robert Rollock)于1583-1599年期间担任爱丁堡大学校长。他的部分神学讲座以《论有效恩召》(Treatise on Effectual Calling)为题,于1597年出版。该书的附录是《小要理问答:论神在起初向人类启示两个盟约的方式》(a Short Catechism concerning the Way in Which God from the Beginning Revealed Both Covenants to the Human Race)。英文译本在1603年出版于伦敦。罗洛克沿袭了神所有话语都是盟约话语的观念。“在盟约之外,神不对人说话”。显然工作之约的教义已经比奥利维亚努斯更加清晰了。“在神按着祂的纯粹和圣洁的形象创造了人、并将祂的律法写在人心上之后,祂就与人立约,在这约中,祂应许要赐给人永远的生命,条件是以圣洁和美善的工作回应神创造的圣洁和美善,并顺服神的律法。”在工作之约中有双重的义:一个是此约的根基,另一个是要产生出来的。在工作之约以外,律法已经存在,即使不作为盟约规则也应当被遵守。在第一个约中,善工并非真的可以赚取功劳,纯粹因为神白白的恩惠而有丰厚的奖赏。我们很容易可以看出,它的主要特征在这里已经被刻画得非常清晰。一会儿我们还会回到罗洛克。
我们无法详细考察卡尔莱特1616年在伦敦出版的《基督徒的敬拜》(Christian Worship),但从其他地方我们知道,它采用盟约教义的经纬编织而成。从那时起,且不说诸多偶尔提及盟约的人,光是专门讨论盟约的著述就连绵不绝。及至威斯敏斯特大会时,最重要的作品是:《新盟约或圣徒的产业,论在恩典之约中神的丰盛与人的义,约翰·普列斯敦关于创世记17:1-2的十四篇讲章》(The New Covenant or the Inheritance of the Saints, a Treatise about the All-Sufficiency of God, and the Righteousness of Man in the Covenant of Grace, Presented in Fourteen Sermons on Genesis 17:1-2, by John Preston),初版于1629年。根据书的扉页,普列斯敦是国王牧师和剑桥以马内利学院院长。他的作品具有更高的实用性,但是在精细的神学分辨上,他不如罗洛克有恩赐。
我们对托马斯·布雷克(Thomas Blake)毋庸多言。他那详尽的著述名为:《为盟约辩护,论神与人所立之约及其不同类型和等级》(Vindiciae Foederis, a Treatise about God’s Covenant Made with Man, in its Various Types and Degrees),1633年初版,1658年大幅修订及扩充再版。布雷克思路清晰。他处理了盟约教义引发的所有棘手问题,以多样化的风格探讨它们。他以令人钦佩的一致性展开他自己的观点,有时候恰恰因为这种一致性而不能总是被人接受。他因为明确坚持一种外在盟约(an external covenant)的教义而具有独特的地位。
著名的约翰·巴尔在不止一本书中对盟约教义作出贡献。在威斯敏斯特大、小要理问答取代所有要理问答前,他写过两个广泛使用的要理问答。此外他还写过一个单行本:《论恩典之约》(Treatise on the Covenant of Grace),出版于1645年,在他去世后五年。该著作详尽探讨了恩典之约的各个连续时代。救恩的经世/施行进程(economies)位于显著地位。应许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带领下的以色列之约、大卫之约、被掳后之约以及新盟约,都依照顺序得到了讨论。巴尔在某些论点上会令人想起柯塞尤斯,比如,他认为基督中保所作的真实补赎(real satisfication),对那些已经在天上之人的状态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由于他的著作出版于威斯敏斯特大会的会期当中,正好是大会致力于建构信条之时,也因为《威斯敏斯特标准》确实借鉴了巴尔,我们自然会料想,在信条对盟约教义的制定上,巴尔的影响力应该可以被人察觉到。
另外一个虽没有参加大会,却毫无疑问对《威斯敏斯特标准》的制定也有巨大影响力的人物,是爱尔兰阿尔玛格(Armagh)大主教雅各·乌瑟尔(James Ussher)。1615年他起草了著名的《爱尔兰信条》(Irish Articles),其中就有工作之约,和被称为“第二个盟约”的恩典之约。该信条中最重要的一些段落,有时候被原封不动地并入到《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中,连顺序都没变。乌瑟尔整理自青年时代各种素材而成的《教义神学》(Body of Divinity),对《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教义神学》1645年出版于伦敦。它对盟约教义的处理,与《爱尔兰信条》是一致的。
威斯敏斯特大会之后出版论及盟约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弗朗西斯·罗伯特(Francis Roberts)的《圣经的奥秘与精髓,即堕落前神在第一亚当里及堕落后在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里与人所立的盟约》(The Mystery and Marrow of the Bible, i.e. God’s Covenants with Man in the First Adam Before the Fall, and in the Last Adam, Jesus Christ, After the Fall,London, 1657),这是一本用小对开纸印刷、且不少于1721页的作品。其中,强调救赎经世进程的倾向,也同样清楚地浮现出来。比起他对各个不同阶段的冗长教义论述,他在一般性地(尽管一如往常仍然是足够细致地)谈论盟约上所花的篇幅要少得多。圣约次序也与巴尔一样,即:1)在乐园中;2)与亚伯拉罕;3)在西奈;4)与大卫;5)与被掳的以色列;6)新盟约。
二、改革宗神学的基本原则
那么,该如何解释盟约观念从一开始就在改革宗神学中占有如此显著位置呢?在改革宗神学的起点上,一定有什么东西使它感觉到自己被盟约观念所吸引。有人可能会说,这个问题纯属多余。盟约教义源自圣经。它是宗教改革回归圣经的精神所带来的,因此除了这个自然的解释之外,无需它求。但这样的回应完全不能使人满意。路德宗和改革宗都一样倚靠圣经。尽管如此,我们现在充分认识到,在处理圣经的丰富内涵上,后者比前者更为成功,这个事实反过来也要求一个解释。因为改革宗神学抓住了圣经最深邃的根基性理念,因而它可以从这个核心点出发,更整全地处理经文,并使其每个部分的内容都各得其所。
这个根基性理念,这把打开圣经丰富宝藏的钥匙,就是神在一切受造物中无与伦比的荣耀。所有关于路德宗和改革宗传统之区别的解释,最后都将归结为一点:前者从人开始,后者从神开始。神并非因为人而存在,而是人因为神而存在,这是铭刻在改革宗神学殿堂入口处的原则。而一旦这个原则应用在人身上、应用在人和神的关系上,就立刻分为三个部分:1)人一切的工作都必须依赖神先在的工作(an antecedent work of God);2)人在其一切工作中都必须显明神的形象,成为彰显神之美德的器皿;3)显明神的美德,不能是无意识地或被动地,而是必须通过理解和意愿,并通过有意识的生活,积极主动地得到外在的表达。我们希望说明,这三个要求如何恰好贯彻在盟约教义中。以下将依次讨论:工作之约、救赎之约、以及恩典之约。
三、盟约教义的阐释
1、工作之约
只要对比一下在不同神学传统中所发展出来的、对人之原初状态的表述,人们对工作之约教义之看法的重大根本差异就立刻会浮现出来。按照路德宗的说法,人已经达到了他的命定,这是因为神已经将他放在一个正直的状态中;他已经拥有永生;在他的处境中,人的最高理想已然实现;无需再做什么以实现神造人时的意图。诚然,人是可变的,他有可能从原初正直、蒙福的状态中堕落。但是对路德宗来说,这并非前瞻性地指向其他东西的阶段,反而是普通、正常、可以预期的阶段。由此可知,在恩典状态下(也就是基督带给堕落之人的状态),一切又回到了原点。很显然,既然在亚当堕落前,人类已经达至其命定,基督所做的就不过是恢复在亚当里所失落的,别无其他。而且,既然已经达至的终极状态与可变性和堕落的可能性是完全兼容的,那么,被基督得回的罪人,就必然只能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因此,路德宗神学相当前后一致地教导圣徒可能背道。它根本不反对将这种称义并得为后嗣的状态,与这种背道的可能性结合在一起。
这和伯拉纠主义者以及所有具有伯拉纠主义倾向之人的情况完全不同。按照他们的看法,人受造时也已经被赋予了最高和最宝贵的事物,但这却不是在路德宗意义上的“内建的圣洁”(a built-in holiness)。伯拉纠主义者不谈这种意义上的神的形象,他们所谓神的形象不包括灵魂的属灵能力本身,而这正是路德宗强调的。然而按照伯拉纠主义者的看法,恰恰是缺乏这个部分,才给人带来了尊严:他是一个自由的个体,必须努力提升自己,以脱离道德中立的状态,而且必须藉着某种伦理性的创造力达至圣洁。因此,他已经是他所当是的,因为他的命定无非就是不确定的自由选择。同样的原则也在恩典的领域贯彻到底。一开始最重要的,在基督的恢复中,仍然还必须是最重要的。这里可以看出,这完全没有为真实的补赎留下空间。基督所能做的,不过是为人挪去他运用自由意志的障碍。他只是再次给罪人一次从头来过的机会。
改革宗对人原初状态的看法导致一种完全不同的结果。他处在一种“完美正直”(perfect rightiousness)的状态中,知道何为善、且有意识地行善。只要他留在这个状态中,就可以确保神会施恩。到这一步为止,改革宗的看法和路德宗一样。但比起后者满足于继续、并无限扩展这种状态,改革宗的观点则专注于一种更高的状态。它不把人看作从一开始就被置于永恒的福佑中,而是将人看为被摆在一种有可能达至永恒福佑的境地。伴随着他不稳固的自由(mutable freedom;直译作“可变的自由”),犯罪和死亡的可能性仍然在他身上徘徊不去。他出于他良善的本性还是可以自由地行善,但他尚未达至只能行善的最高自由之境,后者乃是作为一种理想摆在他面前。获得它的途径是工作之约。同样,恩典的状态最终也要受“人在原初正直状态中之命定”这个观念所限定。我们从第二亚当那里所继承的,与其说是在第一亚当那里所失去的,远不如说是第一亚当本该为我们赢得的——倘若他未曾堕落,而是在此状态中得到确认的话(confirmed in his state)。被置于那个状态中的人,将永远不会从其中堕落。与基督是完美救主同样确凿无疑的是,祂必将“圣徒的恒忍”(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赐予我们。
我们若回顾改革宗原则的三重应用,马上可以看出,单是工作之约就满足了其中的要求。要是照着伯拉纠主义,我们就废掉了人“本有的圣洁”(increated holiness),而允许受造物自己创造出这种圣洁来,我们也就是在否认“人一切的工作都必须依赖神先前的工作”这项要求。这时,创造善的工作就不再属于神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按照路德宗的说法,人被造时立即获得了最高层次的福佑,我们就忽视了第二项要求,即督促受造者的人生目标,当由“在万事上以荣耀神为更高动机”这一点来主导。路德宗的视角明显是基于人论(以人为中心)的动机。这显明了神本体中为父的那一面,但没有达到全面展示神全部美德的地步,更不用说去满足“藉着人有意识的生活,积极并外在地表现神的美德”这项要求了。改革宗的表述在每个方面都与此不同。首先,我们强烈地体认到神先在的工作(antecedent work)。人无法为自己创造善,而是必须发展他里面被神赋予的善。若他天然的良善已经是神创造性的工作,神将他摆在盟约关系中就更是如此了。这同样是神自由行动的产物,是从耶和华俯就的恩典中流淌出来的礼物。全能者从无有中将被造物召唤出来,使他存在,他自己并没有带来任何的权利,至少没有不会失丧之永生的权利。若有一条路可以使他得着这永生,那一定是神的创造,按人的话说,神完全可以省略这一步。我们必须看清楚这一点。按照改革宗的观点,工作之约是超乎神和人之间既有之自然关联的东西。《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以极为优美的方式阐述了这一点(第七章第一条):“神与受造物之间的差距大到一个地步,尽管有理性的受造者都应当以神为他的创造主而顺服祂,但是他们绝不能从神得着什么,作为他们的祝福与赏赐,除非在神这方面自愿以某种方式降卑;祂也确实愿意这样做,而祂降卑的方式是立约。”
如果我们没有搞错的话,一些人对工作之约本能的厌恶,乃是来自于缺乏对这个美妙真理的欣赏。确实,如果亚当与神之间的关系纯粹是一种天然的关系,其中没有任何正面积极的内容,那么作为纯粹表达这种天然关系的盟约理论,确实看起来很不自然。但事情的真相是,在工作之约中,这种天然关系是被用来达成一个积极的目的,不是被抛在一边,反而是被纳入一个更高的目的。由此可知,就算这更高的目的失去效力或归于无有,这个天然的关系却仍然存在。人作为受造物要服从神,而且,即便神无意以永生来奖赏对律法的持守,对人的要求也不会失效。“你要遵行!”仍是正当的要求——即或没有伴随着“就必因此活着”。在恩典之约中也是如此。有份于其中的人,律法的要求就不再是他获得永恒福佑的条件,却仍然是他道德生活的准则,而不能不遵守。
因此,工作之约以一种惊人的方式满足了前述第二和第三项要求。人在他所有的盟约工作中,会彰显神的形象。正如神的有福状态(blessedness of God),在于祂值得敬拜之本体内三个位格彼此之间的自由关系,人也当在他和神的盟约关系中找到他的福分。能反映出神的永恒福气的(这福气是人所期盼的),不在于欢乐本身,而在于他的救恩。因此,他不能立即且过早地拥有最高的喜乐,而是必须沿着一条理性的道路被引领到那里。在他里面的神的形象,必须在他彻底清晰的自我意识中表现出来。在某种意义上,神的形象必须得到扩展,因为人在神的形象中仍有可能犯罪和死亡,这样的人就不再能佩带这形象。在他的一生中,这个形象必须藉着持守神的律法而得到塑造。藉着深厚的道德诚信,他立刻被导向造物主的荣耀,而非他自己的欢乐;他被赋予一个职责,以至于当他尽了本分之后,就能进入与他立约之神的完满喜乐中。
2、救赎之约
如果人在堕落之前就已经和神拥有一种盟约的关系,那么可想而知,盟约观念在救赎之工中也将是主导性的。规条一旦设立,就算人犯罪、背叛,神也不会就这么轻易地放手,而必要藉着贯彻这些规条来彰显祂的荣耀。当我们把中保的职责也放在这个亮光之下,就可以看出它不过是工作之约的另外一面而已。这就可以谈到Pactum Salutis(救赎之约),一个和平筹定(Counsel of Peace),或救赎之约(Covenant of Redemption)了。我们有两条出路:要么否认盟约协议是人获得永生的一般性原则,要么承认这一点,那么他就必须把藉着中保获得永生,同样视为盟约协议,并同意这背后有盟约的设立。如此我们就会清楚地知道,为什么否定工作之约,往往会与缺乏对和平筹定的重视携手并肩了。
救赎之约不过是要证明,就算是源自神至高无上之意旨的救赎工作,还是按照盟约的方式,以自由的行动来执行的。若中保(the Mediator)基督是预定的对象,那作为担保人(guarantor)的祂,也同样是自由行动的主体,祂渴慕按照神的旨意去行,且出于祂与父所同享的荣耀,说到:“看哪,我来了!”与其说盟约观念在此是以一种牵强的方式提出的,倒不如说只有在这里才将盟约观念完整地表达出来。因为只有在三一神的本体(triune Being)里,盟约观念所要求的那种完全的自由,才能真正占据主导地位。这里的盟约完全是双方面的,然而即使是在堕落前,这个盟约仍然只能被当成是单方面的,意思是说,作为神的臣民,人有责任必须按照神所提出的盟约行事。尽管救赎之约现在可以被包含在神的筹定之内(因为它是在三一神里面运作的),它仍然不应该和“预定”(predestination)混为一谈。神学家们很清楚知道如何区分两者。他们不将其放在“先定”(foreordination)的主题下,而是在这之后给它一个独立的位置。他们也在处理谕旨之执行(execution of the decree)的章节里讨论它,这样就可以跟在违背工作之约的教导之后,并开始讨论恩典之约。这是正确的。在预定这件事上,三个神圣位格共同行动,但就救赎的经世而言(economically),预定被归属于圣父。在救赎之约中,他们彼此具有司法上的关系。在预定这件事上,只有单一、不可分割的神圣意志。而在和平筹定中,这个意志表现为在每个位格中都有自己的存在形态(mode of existence)。人不可以基于神本体的统一性而反对这一点。强调统一性到一种程度,使得每个位格之间无法彼此有司法性的关系,就会导致撒伯流主义(Sabellianism),并破坏整个救赎经世及其位格与位格之间的关系的真实状况。人应当考虑欧文在他关于希伯来书的作品中为消除这种异议所说的(Exercitation XXVIII, 1, 13; 参:布雷克,《基督徒理所当然的事奉》,VII, 3)。
现在我们进一步思想,救赎之约的教义是如何考虑“神的荣耀”这个要求的。堕落后,人再无可能以一种讨神悦纳的方式来工作,除非这项工作是神自己完成的,且又是代表人完成的。人已经永远无法凭其双手来赚取永生。在他里面主观发生的一切,都只能是永生本身的原则与现象,而绝不可能是永生的先决条件。获得永生因此终归要倚靠神,唯独是祂的工作,在其中彰显出祂的荣耀,而且在其中没有一样可以归功于受造物而不减损神的荣耀。在这一点上,整个改教阵营,无论是路德宗还是改革宗,都反对罗马天主教,因为它未能看重这个基要的真理。但是驱使两者如此抗议的原因却不尽相同。在路德那里,原因是不安的良心渴求平静安稳,这在罗马的因功得救中找不到。只要罪人自身还必须为蒙赦罪做些什么,他的工作就不稳固。因此sola fide(唯独信心)就成了德国宗教改革的试金石(shibboleth[示播列])[2],称义成为其根本教义。我们会同意,尽管这个教义是以完全的纯净发展出來的,并且以其成熟的形式重新赐给了教会,但它仍未达到那个最高的视角,也就是圣经本身看待这个问题的视角——借用保罗的话说,亚伯拉罕“将荣耀归给神”(罗4:20),圣经藉此看到了他信仰的核心。甚至对称义的教义本身来说,路德宗的把握也不够完整,在其中涌动的不纯粹是神学性的(theological)动机,反而部分是人学的(anthropological)动机(译按:前者是指以神为中心,后者是指以人为中心)。改革宗却非如此。他们同样感到有必要从罗马因功得救的狂浪中脱身,重新站立在稳固的根基之上。但伴随并超越这种必要性的,还有一种更深切的热望:渴求神的荣耀,而非首先考虑自身的平安。改革宗将获取救恩的能力完全从人的手中夺去,如此,才不会缩减神在救恩中的荣耀。对改革宗来说,重要的是神藉着拯救罪人来荣耀自己这件事得以实现;而对路德宗而言,只要确保人没有把任何属他自己的、不稳固的东西掺杂进来,他们就满意了。对改革宗来说,重心并不在于称义自身,而在于判断称义的原则,这个遍布在圣经里的原则教导我们,从整体上说,救恩当被视为唯独是神的工作。
在这一点上,改革宗原则和救赎之约的教义是环环相扣的。没有什么比揭示救恩乃源自神圣存有者自身的深处,可以更强烈地表达出:救恩乃是神的工作,祂要藉此得着荣耀。发出救赎要求的是神(以圣父上帝的身份),为履行这要求而成为担保人的也是神(以圣子上帝的身份),将救赎施行出来的还是神(以圣灵上帝的身份)。在永恒的大光中(住在其中的只有神),神为我们拟定了救赎的进程,这个进程的轮廓是纯一的,也不会被人手的任何助力所污染。这是三一神的创造,万有都是本于祂、倚靠祂、归于祂。
如此一来,盟约教义在和平筹定的教理中找到了它真正的神学支撑点。只有当我们清楚明白它如何根植于神的本体,而非根植于在创造后才存在的事物,直到此时,才算是找到了这个支撑点,也只有到了此时,我们才能神学性地(theologically)思考盟约的观念。工作之约也部分显明了这点,而最明显的地方,就是存有的次序如此优美地反映在工作的次序中,三一神的三个位格本身也共同参与在一个完全属神的盟约内。尽管如此,盟约教义在其最初发端时,还是离弃了从人着手考察自身周围的倾向。藉着总结出和平筹定的教义,这一危险得以被避免,神被置于中心。在此,同样地,受造物的一切关系应当是彰显神之美德的途径这个要求也得到了满足。
对于救恩的施行来说,救赎之约也是有意义的。它确保神救赎之工的荣耀会被印在选民的意识之中,并透过他们的生活主动表达出来。这只有当基督的工作被完整地施行在选民身上才有可能发生,而这完全是因为基督的缘故,也是选民与基督联合的缘故。只有当信徒理解到,他如何必须、也已经从中保那里领受一切,神如何不可能藉着基督以外的途径来对待他,只有这时,神藉着基督所作成的荣耀大工的图景,才会出现在他的意识中,恩典的宏伟理念才会占据主导,并且在他的人生中成形。因此,对改革宗来说,以重生为开头第一步的整个ordo salutis(救恩次序),都系于与基督的奥秘联合。没有任何福气祂未曾赚得,也没有任何福气不是由祂赐予,或虽由祂赐予却没有提升神的荣耀。救恩次序的基础不在其他,就在于与基督所立的救赎之约。在此约中,父所拣选的人都给了基督。祂成为此约的担保人,以便将他们植入祂的身体中,好叫他们藉着信心活在恩典的思想世界中。基督施行救恩,而且是祂主动地施行救恩,是改革宗神学的一个基础性原则。改革宗神学也正确地将这种施行视为一种落在中保(the Mediator,中介人)身上的盟约性要求,祂为完成这项要求而成为担保人(the guarantor)。以这种方式,改革宗神学只是再次表明,它不以任何为满足,除了那句包罗万象的口号:恩典在罪人身上的工作是神荣耀的真实写照。
在此,让我们再瞥一眼这个教理的历史。伽斯(Gass)有一种观点,认为柯塞尤斯唯一引入盟约系统的新奇观点,就是将盟约的概念应用在三一神的三个位格上。然而正如其他的观点,此处被归功于柯塞尤斯的观念其实来源更早。要想追溯某个教义的发展,人需要注意不应过分重视名称,不要因为尚无后期的通行格式,就过早地下结论说以前没有它。固定表达通常只会出现在发展的末期,而非开端。如果我们这样考虑问题,就必须认同海珀的看法,他与伽斯的看法不同,将这个观念归功于奥利维亚努斯(《敬虔主义与神秘主义史》,211页)。在奥利维亚努斯那里,圣子担任永恒担保人职分的观念,已经充分并清晰地表达出来了。在《论盟约的本质》(De Substantia Foederis)的23页,他写到:“神的儿子既已被神委派为盟约的中间人,就在两个理由上成为担保人:1)祂需要补赎(satisfy)所有父所赐给祂之人的罪;2)他们既然已经被植入在祂的里面,祂还要完成这个目标,就是他们要在他们的意识中享受自由,并一天天地更新为神的形象。”人们应当注意,圣子的担保不只是被描绘为盟约的前提条件,更是盟约施行与运作的根基。对奥利维亚努斯来说,这不是一个抽象的理念,反而是支配着他整个的神学表述。藉着应许和起誓,神将祂自己赐给我们、作我们的神,收纳我们作神的儿女、永生的后嗣。应许和起誓都是对基督作的(祂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也是对所有被植入这位子孙里面的人作的(De Subst., p. 2)。作为祂担保的结果,这位中保塑造了祂和选民的完美合一,并且,当祂成了肉身并受了苦难,这受难就可被算为祂身体的赎金。主的复活是所有属祂之人真实的无罪开释(actualis absolutio)。人们应当比较海珀《德意志更正教教理学》(Dogmatik des deutschen Protestantismus)第二卷215-220页的各类引证。海珀从他的概述中得出以下结论:“由此显出,奥利维亚努斯之救赎教义的重心,确实是圣父与圣子之间的pactum and consilium salutis(拯救协议与筹定)教义,以及依赖于此教义的另一教义,即:将选民植入基督,或者说植入在基督奥秘的身体里……这个在永恒中已经确立的关系有如下性质:自永恒中,父神看圣子就不是别的,而是要成为肉身的道,并要与组成祂奥秘身体的选民/信徒联合。”(218页下)
这个思路可能导致奥利维亚努斯在恩典之约的实质和见证之间做出区分。盟约实质或本质乃是在于中保的工作,而见证则是中保藉着圣道和圣灵与我们建立一种活泼的联合时,被带给我们的。
如此表达的理念至今仍然是有效的,要跟随这个教义的发展之路,也不会花费太多的气力。罗洛克已经证明,基督中保在恩典之约里的工作,为何不过是在亚当那儿被破坏的工作之约,却在祂里面被成全了。“因此,我们的中保基督,为了我们益处的缘故,使自己顺服在工作之约下,也顺服在律法以下,既在祂圣洁、良善的一生中成全了工作之约的条件……又忍受了咒诅(就是当人没有守住良善、圣洁之工的条件时,在工作之约中被威胁所要受的咒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两个方面看见基督顺服在工作之约下,即在祂的行动与受苦(doing and suffering)上,而且在这两方面祂都完美地成全了,为此祂也为了我们的缘故,成为我们的中保。”(Rollock, Works, I, 52f.)
对于英格兰清教徒、1622年起任弗兰内克(Franeker)大学讲师的埃姆斯而言,救赎之约是用来反驳抗辩派(Remonstrants)的武器。埃姆斯基于以下两个理由,拒绝亚米念主义对救赎之完成与施行所作的区分:1)它假设神的谕旨的效力,有可能受到挫败或被剥夺;2) 它使与基督所立的盟约(“祂必看见后裔,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祂手中亨通。”Anti-Synodalia. De Morte Christi, I, 5)变得毫无能力。因而,与神的谕旨一道,在救恩的完成和施行之间,救赎之约在此表现出更高的合一。英语世界的神学家们尤其从这个角度处理这个教义。普列斯通把恩典之约的应许分为两类,一部分被视为给基督的应许,另一部分则是给信徒的应许:“经上说,‘这应许是对那位子孙说的’,然而这应许是给我们的,同时这盟约又是与亚伯拉罕立的:所有这些如何能同时成立呢?答案是:给那子孙,即基督本身的应许如下:汝当为永远之祭司,吾将赐汝大卫之国;汝当坐其国位,汝当为和平之君,政权必担于汝肩,汝亦必为吾民先知……这是给那子孙的应许。对我们所说的应许虽然在同一个盟约之中,然而在这方面却是不同的,主动的部分托付给了弥赛亚,那子孙本身,而被动的部分是由给我们的应许所组成的:你们将要受教,你们将说预言,你们的罪将要得赦免……因此应许是对我们说的。应许又如何是对亚伯拉罕说的呢?经上说,‘地上万国必因汝得福。’意思是说,它们是衍生的应许。首先与原始的应许,是对耶稣基督说的。(Preston, The New Covenant, ed. 1639, pp.374-5)”
其他许多人也表达了同样的想法。动机来来回回都一样,就是将救恩的施行聚焦在基督身上,我们很自然应当永远记得的是,基督乃是藉着圣灵工作。瑞诺德(Reynolds)说得精彩:“凭信心所相信的每一个应许,都引导人归向基督,使人思考我们与祂的联合。我们只能藉此享有诸般应许,正如一个圆的圆周上的各个不同点,无论彼此相隔多远,都可以画出相交于中心点的线条。”即使是布雷克,尽管他强烈否认任何内在的盟约(internal covenant),也并不否认救赎之约的存在。他承认在父和子之间有一些盟约性的交易(federal transactions),他也承认这是为了我们的缘故,并且最终,恩典之约的经世以及我们身处此约之中,乃是建基于救赎之约(Vindiciae Foederis, pp.14f.)。
克洛彭博格以最精确的方式阐述了救赎之约的教义。在《论神的盟约》(Over het Verbond Gods, Disputationes, III, 4; Opera Omnia, I, 503)一书中,他说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基督在路加福音22:29所说的,新约(恩典之约)的双重盟约(diatheke)或时代(dispensation)。1)一方面是圣父藉着盟约向担保人所定旨的;2)另一方面是子作为父的担保人,为我们的缘故,定旨了生命与属天荣耀的应许。就第一重协议来说,此约被说成是由神在基督里面预先立的(加3:17)。在这里有完整的盟约观念,即出于互相信任之双方的协议。至于第二重协议,此约被称为由那即将过世之人为我们所立的遗嘱(来9:14-17)。”于是,克洛彭博格接下来首先说到父神和作为担保人的圣子之间的盟约协议,而我们被视为与后者是一体的。他的特殊之处乃是在于,他选择了盟约教义作为他和抗辩派争论的一个起点。
从以上的快速浏览可知,救赎之约的教理并非拣选教义的修订而已。其价值不在于可以把此约拉回到神的谕旨中去讨论,而在于将此约的焦点集中在中保身上,并且一方面证明在祂里面,救恩的成全与施行的合一,另一方面也证明盟约的各个不同阶段。由此可知,尽管人们通常以为神学家们所强调的是此约在永恒里的超越性,但事实上神学家很少这样强调,而且,尽管它被称为是永恒的约,但这种永恒性与谕旨的特性还是有所不同的。说它是永恒的,乃是因为它是落在三一神之内,落在存在于永恒中的神圣本体之内,而非它被提升超过了历史现实这种意义上的永恒:“正如人类犯下了双重罪恶,”奥利维亚努斯说,“圣子既已被神定为盟约的中保,就在两方面成为担保人:祂必定会补赎,等等。”弗朗西斯·罗伯特则如此定义:“信心的盟约是神仁厚的契约或协议,是在人堕落后,与耶稣基督(末后的亚当),并在祂里面与祂所有的后裔订立的,为要藉着基督,使他们从罪和死亡的状态中,恢复到公义和永生的状态中;在祂里面,耶和华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祂的子民;他们得以藉着真信心,领受基督和约中的一切怜悯,并照着福音,行事为人与这一切的怜悯相称。”(69页)
救赎之约是一个新发明,这个立场早已被韦修斯(Witsius)在他的《盟约的经世》(Huishouding der Verbonden, I, 2, 16),和早于他的罗伯特在《神的诸约》(God’s Covenants, II, 2, 3)中所驳斥了。我们绝不能忘记,这个教义同样有其历史。它并非直接和整个儿地取自圣经,而是从中生长出来的。柯塞尤斯之后的盟约神学家们对它的描绘,有时候太过人性化,从解经上来为它辩护也不总是令人满意。但是,仅就其核心而言,它乃是相当稳固地建基于改革宗神学的原则,也已经遭受过各种攻击,并且,尽管它具有超越性的特征,它在信徒的心中却为自己保证了一个永久的位置。
3、恩典之约
若救恩之工在其根源就采取了盟约的形式,那么,它接下来的展开就必定要与之相对应,也要以一种立约的方式来进行。救赎之约并非是孑然独立的,而是整个拯救经世的根基。在圣经中,这是回荡在永恒里,并一直奏响进入我们所在之时间里的宏伟序曲,在这个序曲中,我们已经可以听见恩典诗篇的纯净曲调。因为神从起初就将自己设定为要付出爱与信实,就像人对他的朋友一样,也因为祂已经藉着祂的爱子将自己盟约性地委身于修复被破坏的信实,因此这个盟约性救恩的施行,也必当沿着相同的脉络来进行。救赎之约是恩典之约的模板,但又不止如此,它还是后者得以实施的有效因。就其邀约与施行而言,恩典之约是被包括在和平筹定里的,以至于后者完全可以说是一份礼物,一个盟约性的好处。藉着自身被正式任命、被膏立为救赎之约的中保,圣子从万古以来就统治着恩典之家,藉着圣道与圣灵将教会召聚在身旁,并对所有渴望按照祂的律例而活的人,提出所有权的要求。而无论恩典之约的范围要划得狭窄还是宽泛,它总是牵涉到与基督的关系(无论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藉此它与救赎之约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也不该认为,中保(作为属祂的百姓的担保人)在此盟约中的出现,会妨碍了他们与神建立盟约的关系。圣子成为担保人,显然是为了使他们能够以立约当事人的身份为人处事,以至于基督不但将自己的功劳归算给他们,更将他们按照神的形象重新创造(re-creation),并在他们的心境和生活行动中,使神的恩典得着荣耀。他们绝不会被排除在神的恩典之外。就算亚当的替代性角色,也不会妨碍任何人以自己的良心,亲自对工作之约的破坏作出反应;基督所作的担保,就更不会拦阻任何信徒在他自己和神的关系中,经历恩典之约的展开。正因为圣经从来没有打算要将恩典之约松散地与和平筹定并列,一个人的表达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就只是偏好的问题。尽管有些人选择把这些内容分为两个约,其他人则将它们包括在一个约中,但他们总是意识到,这其中的差异不是原则上的,而只是方法上的。《威斯敏斯特标准》为此提供了一个决定性的例证:《信仰告白》论及神与在基督里的信徒之间的恩典之约,与此同时,《大要理问答》则将恩典之约表述为与身为第二亚当的基督所立的盟约。
(1)人有义务接受并回应神的恩典
在神完成的工作的基础上,盟约关系随之展开,这就是ordo salutis(救恩次序)丰富内涵的本质。还是那句话,神的荣耀要在信徒的意识和生命中彰显出来,似乎在每一点上都是解释盟约概念最重要的思想。对于“中保所获得的救恩,如何被个别的信徒转化取用(appropriation)”这个问题,改革宗信徒的回答是:乃是以最能彰显三一神在救恩工作中的伟大和荣耀的方式。人不是直接、立刻获得全部的福分,否则他就没有机会看到奇妙之恩典计划的展开过程。恩典也不是像materia medica(治疗药物)那样,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被一点一滴地注入到罪人体内,否则他就不能欣赏恩典的神圣之美。神所恩待的罪人的真实处境,必须被显明在他的意识中。因此,改革宗基督徒喜爱透过有意识的人生表达恩典之工。他们时常会谈及“大能的呼召”,有时候这意指重生。所以他们并不否认,要在死人的灵魂里创造出属灵的生命,就必须有神直接的行动;但他们更愿意尽可能强调,只有意识到神的恩典,生命才能收获最丰盛的果实,达到其命定。圣道是神用来对意识工作的食物,因此,若无圣道,这工作就不是神的。
这些想法很容易借由盟约关系的观念来总结。从外在呼召开始,神与人打交道的方式就透露出这种观念的蛛丝马迹。可以说,它在道德责任的光照下,就变得里外透明了。甚至对救恩的描绘与传讲,也是为了使人充分意识到他和神之间的关系,为了刺激他的意识,使他自由地回应以盟约的形式临到他的、神俯就的良善。藉着改革宗对人里面神的形象的宽泛和狭窄含义所作的区分,使这点成为可能。路德宗认为神的形象主要存在于灵魂的道德品质中。而按照改革宗的理解,这两者无法辨认。人有理性和意志,他是灵,他能认识神;在这方面,他也是神的形象。堕落之后,这些能力多多少少还是存在的,在这个程度上,他仍然是神的形象。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把任何的良善归给堕落之人,而是要透过他本体的最深幽处和他真实的命运,将他描绘为这样的一种人:他必须领受神的荣耀,并容许它藉着自己透照出来。
凡是将这一点谨记于心的人,就不难理解,为何对改革宗神学家而言,连同盟约概念一起宣讲律法,具有和对路德宗而言不太一样的重要意义。后者几乎不允许律法在堕落前占据一席之地。无论重生之前或之后,律法都仅有消极的特性,只是为了引发悔改,治死老旧的罪人。对改革宗来说,律法也有这个目的,但不是全部。即使是那些严格区分律法和福音,并将后者完全视为应许的神学家们也仍然强调——事实上,这些神学家比起其他人更强调——作为人生的全面规范,律法也决定了人与福音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我们观察到改革宗观点所具有的强烈的道德严肃性。在人的生命中,但凡神的律法无法直接适用、并对他的良心产生深刻的印象,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一旦福音入到人的意识,他就要面对信心的要求。没有一个罪人能有一刻从他对福音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ward the gospel)中脱身,只要他的良心还约束着他。正如堕落前的人有义务缔结工作之约,堕落后的人更有义务以一颗信靠的心接受恩典。当然,不同的是,在正直的状态中,接受是理所当然的事,而在堕落状态中,除非有超自然的恩典,否则这不可能发生。
改革宗神学对律法的看法受盟约理念影响的地方还不止这些。即使在堕落后,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它的盟约形式。律法不可能被包含在盟约关系中却不受其影响。直至今日,律法的呼喊仍在我们耳畔回响:我将给你如是人生,惟愿你可以成全我!在工作之约遭到背弃之后,神大可以全然根除此关系,将最后一点痕迹从我们心中抹去。然而,他却让我们永志不忘。他以假设性的方式不断重复那应许,结果就是,他把藉着持守律法来获得永生的理想不断地摆在我们面前;尽管这是一个已经失落的理想。因此,圣约观念的基本内容一直保留在我们的意识中。当圣灵的工作藉着律法和福音的管道引发真正的回转时,在这回转中,对那失落之理想的渴求就似乎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此,我们也可以解释,为何老一辈神学家并不总是清楚区分工作之约和西奈之约。在西奈之约中赐下的并非“赤裸裸的”律法(the “bare” law),而是对那可以说是在西奈得以延续的恩典之约的惠益中得以恢复的工作之约的反映。
(2)对全备盟约恩典的稳固盟约信心
然而,说上面这些是盟约的本质却是错误的。人与神之间的这个自然关系,和这个由造物主所提出的正当诉求,一直是有效的,也继续延伸到后来的每个阶段,是一切行动的前提,包括恩典之约。只要不会有人以为,这些因素就道尽了恩典之约的全部,再无其他了。使恩典之约成为日常生活之大能的本质,在于另外一个添加上去的因素,现在我们就要来看看它。
为了正确理解它的性质,我们首先要提及以下的特点。盟约神学惯常于从基督徒生活的角度审视真理。这不意味着它停留在一个有限的救恩论范畴之内,因为这么做可就归正过头了;它的目的确实是神的荣耀。虽然有的时候,为了客观性的缘故,个人兴趣会在真理教导中被推到一边,在盟约主义者身上还是体现了基督徒和神学家的合一。众所周知,这体现在《海德堡要理问答》中,那个“相信的我”不断地表达自己。由此可知,盟约观念被认为是只有在信徒中才得到了实现。至于“如何考虑那些缺乏信心却活在盟约职事(ministry of the covenant)下的人”这个问题,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会被提及。盟约神学发展其内容的方法,不是通过将自己放在盟约之前(因此是在盟约之外),而是放在盟约之中。盟约既非一种假想的关系,亦非有条件的地位,毋宁说是新鲜而活泼的团契,恩典的大能在其中运行。这只有通过信心的操练才能变为现实。作为神真正盟约伙伴而行动的总是信徒。因此,那些成为盟约伙伴的人,身为信徒,也有完整的应许作为印证。盟约是一个整体,一切益处无不囊括其中。
基于上述考量,我们可以回头来看看前面所说的盟约教义的主导原则。若情况如此,它不是别的,乃是改革宗信徒对上帝恩典之荣耀计划别具慧眼,且洞若观火。这会在他心中激发出一种盟约意识,并保持其活力,结果是使他对这一圣经的观念如数家珍,这思路对他而言如此自然。若非他能够站立在光的包围中,被光束从四面八方照亮,他怎么能领受并反射神的荣耀呢?站立在这包围中,意味着成为立约的一方,以盟约意识来生活,并饮自约的完满。基督徒知道他在神的盟约里是立约的一方,因此他拥有一切,无论是在时间或永恒中,随时都拥有全备的恩典。藉着信心,他是盟约的成员,这信心视野广阔,包罗万象,不仅指向称义,更指向在基督里属祂的一切恩惠。路德宗倾向于片面地看待信心——只看到它和称义的关系,但是对改革宗而言,信心(在这个词的全部意义上)是使人得救的信心。按照路德宗的说法,圣灵先在罪人里面产生信心(此刻他暂时还未与基督联合);然后称义随着信心而来,也只有在此时,与中保神秘的联合才得以发生。一切都取决于这个仍有可能失落的称义,以至于信徒可以说只能看到少许恩典的荣耀,且可以说只是为今天而活。盟约的眼光与此相反。人先是藉着奥秘的联合与盟约中保基督联结,这使他在信心中产生意识性的认知。藉着与基督联合,万有会在基督里一并赐下。信心也拥抱这一切;不仅抓住瞬间的称义,更紧紧抓住基督,将祂看为先知、祭司、君王,看祂是富足和完满的弥赛亚。这种看法上的差异,最深刻的理由乃是在于,对改革宗信徒而言,最重要的是在信仰的意识中领受神恩典工作的全部荣耀。因此,信心不能被限制在一部分真理的有限范围内,始终盯住它不放,而需要自由和广泛地关注救恩的整个计划。路德宗信徒像小孩子一样,满足于活在父亲当下的微笑中;改革宗信徒则像成人,在其意识中放射出神永恒的荣耀。
如果这诚然是盟约视角的本质特征,那么这种视角就不可能在拣选的观念之外运作。神恩典的源头,改革宗信徒靠盟约得享的全部益处,对他而言都取决于拣选。若盟约意识是改革宗形式之信仰意识的正确表达,那么拣选的观念必然在盟约意识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必然会被这个观念所弥漫,否则它就会缺乏其最深沉、最优美、最珍贵的馨香。如此一来,即使当我们在用盟约教义描画基督徒人生真正的鲜活性时,会发现拣选之恩的血液奔流在这整个人生中。人们最多会说,由于改革宗神学是以实用的方法来处理拣选的教义,它就没有清楚描绘出这教义的黑暗面,即遗弃论(reprobation)。然而,改革宗神学并未怀疑或否定它。至于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说,盟约意识和拣选意识并不是分离的,而且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以下的历史事实提供了充分的证据:盟约概念活在信徒的意识中,以表达恩典状态的确定性。它被用来当作圣徒恒忍教义的一种公式套语,后者无疑根植于拣选。思路是这样的:工作之约的稳固性同时取决于神和人。因此,这是一个暂时而不确定的盟约。而恩典之约的稳固性则单单取决于神,祂要向立约的双方负责,并藉着圣灵使人的意愿和行为生效。它的稳固性并不取决于终点(作为一个要达到的理想),而取决于起点,取决于中保的工作,而这反过来也已经建基在祂永恒的担保上。因此,这是一个永不改变的盟约,会延伸到永恒。这是一个订婚的公告,信徒藉此可以确认他的未来。有人可能会说,这只是从神的角度看问题,因此只能如此理解,即祂总是遵守、并会永远遵守祂有条件的承诺。但这是不可能的,纯粹是因为如此一来,圣徒的恒忍就失去了根基,也因为这种稳固性不能归给恩典之约,和工作之约有别。我们不应忘记,加尔文主义者的宗教改革针对路德宗的回应,必须有利于盟约理念的这种用法。如果对我而言,救恩乃是归结于外在的蒙恩之道(means of grace),那么恩典在我里面的延续和发展,也将取决于外在恩具的使用。因此,路德宗不熟悉圣徒的恒忍(the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却满足于蒙恩之道的持续存在。很多人都特别注意到,他们信靠的是蒙恩之道的保守(a perseverance of the means of grace)。但是当盟约概念被置于蒙恩之道的背后,以至于恩典乃是取决于神的手而非受造之物时,恩典就必须立即表现出一种不可抗拒和不可磨灭的特征来。
(3)作为盟约意识和盟约实现的信心
就成年人而言(因为我们目前是在讨论他们),在神拣选恩典的基础上,盟约预设了藉着信心对盟约内容的接受,以及个人对此内容的转化取用(appropriation),而盟约的施行则是从这一推定开始的。这是在“盟约的邀请”和“立约的要求”之外所添加的第三类、全新的方面。盟约的实现(realization)就此发生。关于这个主题,引用一些著名神学家本人的话应该不算多余。首先,盟约的具体实现(actualization)是藉着使人得救的信心(saving faith)。布林格说(Decades, III, 6):“创世记明确教导我们,谁是立约的双方,即:永活、全能的神……和亚伯拉罕及其所有后裔,也就是和所有相信的人……因为使徒保罗如此解释亚伯拉罕的后裔,特别是在加拉太书中,他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奥利维亚努斯则详细地论证说,盟约并非泛泛地盖印生效,而总是基于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有信心。“因此,人在宣讲圣道时,无论是面对被拣选者还是被遗弃者,都需要提出恩典应许的邀约,并召唤接受恩典的回应。但神只在选民心中成就祂所命令的。为了使教会可以从人类整体中浮现出来(神亲自在基督里使他们合而为一),神就开始这个庄严的协议(好像在一个婚姻契约中那样)。但是祂并不是笼统地以恩典的印记的邀约来开始这个协议(因为很多人公开拒绝这邀约,以至于不可能给他们印记,何况主并不愿与伪善者立约,因为就算神自己首先盖了印,他们也会偷偷地使自己的心变得刚硬),而是在有形记号的基础上,以恩典之邀约的最后一件事开始这个协议,这样,我们就可以和我们的后裔一起臣服于神的命令(祂藉此召唤我们领受所提供的恩典),而非使自己心硬。接下来是为最初在福音中提供的恩典盖上印记,也给神特殊的联结盖上印记。”(Substantia Foederis, II, 54)彼得·马提尔(Peter Martyr)持相同的看法,我们读到:“信心总应当先于圣礼的施行——如果我们希望正确使用它们而非颠倒次序的话。正如没有信心而吃喝圣餐是极不恰当的领受方式,同样,没有信心而受洗也极不恰当。我希望大家知道这是在说成人,至于孩子该怎么办,我们将另行讨论。”(Loci Communes, II, 16, 10)穆斯库鲁斯(Musculus)区分神与全地并其中的动物、走兽并人所立的一般性盟约,和“神屈尊与选民和信徒所立的、特殊而永远的约。这个约被称为是‘特殊的’,是因为它并非与所有人相关,而是只和选民、信徒有关,也就是说,是给信徒之父亚伯拉罕及其后裔的。”(Loci Communes, p. 142)珀拉努斯教导说:“所有信徒共同的盟约是特别在洗礼中,与每一位信徒所立的。”(Syntagma, VI, 33)普列斯敦写到:“下一个问题是,人如何知道他是否在这个约中?……若你信,那么毫无疑问你就是在约里……此外还有别的方法可以知道,就是:‘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若有人被植入到这后裔里,他就要得福。”(The New Covenant, pp. 378, 380)只有布雷克是个例外。他认为盟约的本质在于历史性的信心,他解释说,这使一个人作为成年人有资格受洗,而且只有对将来能使人得救的信心所作的应许,才必须被包括在内,而无需预设有这种信心的存在。(Vindicae Foederis, p. 289)
同样容易证明的是,神学家们并没有以一种二元论的方式,并列拣选和盟约,而是将它们有机地关联在一起。众所周知的是,许多人甚至在他们的盟约定义中,都认为拣选限定了盟约的范围,比如韦修斯、布劳(Braun)、兰普(Lampe)、麦斯崔克(Maestricht)、阿·马尔科(á Marck)、布雷克(Brakel)、弗兰肯(Francken)等人。这种描述不但在后期神学家那里,在非常早期的神学家那里也可以发现。奥利维亚努斯的著作,被冠名为:《论神与选民之间恩典之约的本质》(Concerning the Substance of the Covenant of Grace Between God and the Elect)。赛格丁(Szegedin)论及一种“神自我降卑,与信徒和选民所立的特殊和永恒之约”。(引自:Heppe, Geschichte des Pietismus und der Mystik in der Reformirten Kirche, p. 208)如前所述,穆斯库鲁斯的表达如出一辙。珀拉努斯(Polanus)也无二致:“神仅仅与选民立了(新旧)两约”。(Syntagma, VI, 33)同样,1603年,布莱蒙(Bremen)大学教授玛尔提努斯(他后来提倡一种对多特信经更自由的看法)曾写到:“与某些个别的选民所立的恩典之约,而我是其中一员。”几乎无需提醒,所有这些绝非意味着盟约的施行是从拣选而来,也不是说所有非选民与盟约的施行没有任何关系。不如说它的意思是:1)对一个人的拣选有任何的把握,都必须从强烈的盟约意识中发展出来;2)在施行盟约的整个过程中,人始终应当藉着圣道和圣礼,将神那源自拣选、包罗万象的诸般应许铭记在心;3)最后,盟约的本质,它的完全实现,只在神的真儿女身上显明,因此其范围无非就是选民。第二点尤为重要。事实是,凡神的盟约得到施行之处,皆有其内容的印信:在有信心的前提下,我们就能确信,人有资格获得盟约的祝福。除此之外,我们说,始终有一个庄严的见证和事实的印记,就是神希望这恩约完完全全地实现在所有选民身上。在《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对恩典之约的定义中,这两个方面被很清楚地作出区分:“……恩典之约。在此约中,上帝藉着耶稣基督白白地向罪人提出了生命和救恩的邀约;这约要求他们归信耶稣,以至可以得救,并应许将圣灵赐给一切预定得永生的人,使他们愿意相信,也能够相信。”(第七章第三条)
我们已经看见恩典之约的教义在信徒的良心中,如何完全公平地处理荣耀神的命令,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指出这个教义对信徒积极的生活所造成的影响。信心,若从盟约角度看待,不仅在视野上更为广阔、更为全面,也比从其他方式来看更为强大和健康,因为它承载着善行的基础。在恩典的状态里有一种盟约的义务。出于感恩的刺激必须在被更新的道德意识上动工,以至于借由基督所获得的新生命可以产生行动,得到发展。这与极力强调预定所带来的预期是截然相反的。恩典之约的教义不会宣讲被动性,而是要求严格的纪律,有时甚至达到一个地步,会让路德宗人士担心回到罗马因功得救的教义上去。这种担心并无根据。带来这些感谢祭的,是在祂子民中工作的中保基督。用我们要理问答的话说,连于基督的人不可能不结出感恩的果子。基督必要在祂的子民中荣耀地掌权,因为这是祂劳苦的赏赐。祂不可能保持沉默,在我们里面毫无作为。唯有当我们被祂的圣道和圣灵统治,以致于完全降服于祂,祂的国才能完全彰显。基督是受膏君王,不仅统治教会,也已经作为万有之首而被赐给教会。因此,在全部生活领域中工作的迫切性也取决于信徒的行动(祂的统治乃是透过他们的行动来实现的)。对改革宗信徒来说,因着其盟约特色,基督信仰是一种永不止息的再创造原则,永远不会从世界中退却,反而要为基督征服世界。真正的宣教使命感只可能出自这种盟约意识,因为在宣教行动中,基督的身体会为自身的完全而努力奋斗,除非它所有的成员都已经加入其中,这种完全就无法达成。在缺乏这种思想的地方,宣教的热忱就只会被慈善的动机所驱动,就其本质而言,这样的动机都不够持久和强大。
最后,我们要从另外一个重要的角度揭示改革宗原则和盟约教义的密切关系。这关系到教会的历史性进程。宗教改革运动在这点上是团结一致的,即借由无形的、与基督的联合,而不像罗马那样,借由外在的、可见的约定来寻求教会的本质。这个无形的特性同时也是个体性的(individual)和不可转让的(non-transferable),因此会带来失丧延续性(continuity)的危险。为了防止这种危险,路德在退回到罗马的路上走了很远。在某种意义上,他重新将那维系教会之不可见的、超自然的恩典,囚禁在某些外在的事物里。恩典的能力在圣道和圣礼中;只要教会建立在圣道和圣礼职事的基础上,她就是自给自足的。上帝,一如既往地,放手让恩典保守教会,并将恩典放在蒙恩之道中。改革宗信徒不能满足于这种表述。当然,他相信教会的延续性。但正因为他相信这一点,所以无需借由各类救赎工具(恩典会被浇灌在其中)来支持教会。对他而言,教会的延续性是由上帝信实的应许来保证的。因此,在圣道和圣礼的背后,他将盟约当成最强有力的表述,说明历世历代永不中断的恩典工作,和所有的恩典一样,都如何立基在上帝主权的美意上。教会不是因为我们施洗或者藉着洗礼使人重生而继续存在,更好的说法是神一代代地坚立祂的约,因此教会得以存留,而我们也施洗。既然这是神的盟约而非人的盟约,基督徒就应该藉着无声的感恩,也藉着信心来认识神的良善,并藉着此印记而得刚强。再次,盟约观念要求信心应当自由地、积极地回应神的宣告。盟约诚然把不同的世代连为一体,正如它诚然把个体的人与神连为一体。应许的另一面是感恩的信心。这信心也必须活在教会中,好叫未来的世世代代可以延续下去。它不应该像沙漠一样,当赐福降临时毫无反应;相反,它必须是被一个浇灌的花园,其花朵寻求太阳的面光,叶子舒展以捕捉神恩典的雨滴。显而易见,盟约的观念在其中何等强烈地呈现,并远远超越了对圣礼的偶像崇拜。
在这方面,也可以说,盟约观念也防止了过于狭隘的圣礼观。作为盟约的印记,圣礼拥有和盟约本身一样广泛而全面的重要性。它们不再是特殊恩典的标记,而成为它们所当成为的:全备恩典的特别标记。它们以我们在祂里面所拥有一切,将基督,那丰盛完满的基督印证给我们。我们不可把这印证的大能局限在救恩之道的任何单一阶段上。既非重生,也非称义或圣徒相通,各自独立,而是所有这些,这些共同组成盟约恩典之内容的,是所印证的对象。如果说对盟约的意识像一面镜子反映了神的荣耀,那么所有个别的光束都在圣礼中聚焦,共同指向一个荣耀。
(4)圣约儿童与婴儿洗礼的问题
这对孩童的重要性其实不亚于成人,从上文可知,在盟约的邀约和盟约的义务这两个要素之外,还有第三个要素。这是由盟约儿童必将进入盟约团契的期待所组成的。这期待乃是基于神对信徒的应许,就是祂渴望作他们以及他们子孙的神,祂也同样渴望在他们的后裔身上延续盟约,使之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这不仅适用于某些带有特定限制的应许,也同样适用于涵盖整个人生、包括所有恩典礼物的盟约应许。我们认为,在这方面,改革宗教会如何强有力地应用盟约的全备性特征,是相当引人注目的。他们都一致认为盟约是一个整体,在他们关于敬拜礼仪的作品中,毫不犹豫地完全展现它的丰盛性。作为一个应许性的盟约,其全部内容在一个人还是婴孩时,就已经临到他。而当婴孩后来以活泼的信心进入到盟约意识里之时,这信心将总结包含在盟约中的一切,以至于神的恩典工作之宽广、丰盛的世界展开在他眼前,这是一个既回顾又前瞻的视角。正是这样一个美丽的景象,使得人们称盟约观念为一个“母亲理念”(mother-idea)。盟约是一位母亲,因为她藉着神圣的恩典和应许属灵地生产儿女,使她的儿女从她领受一切,生育、喂养、祝福他们。改革宗神学显然意识到教会有两个方面,除了是信徒的聚集和基督身体的彰显之外,他也必须是添加新信徒的管道。它并没有将这两方面拆开,反而以有机的关联来保存它们。正因为神的应许已经完整地赐给了信徒的聚集,包括他们的后裔,所以这个聚集也是生儿育女的母亲,主也使她因她的儿女而欢欣。与诸如“救恩的机构”这类语词不同,“母亲”这个名称表明了这种真正的改革宗观点。
就我们所知,改革宗神学的主要发言人一致同意这点。他们都认识到,教会已经为了她的后裔领受了这些应许。他们同样认识到,教会对盟约的看法所提供的安慰,其核心就是对这些应许的思考。并且他们坚持认为,记念此应许必须被当做一个急迫的理由来发挥作用,以激发教会的后裔凭信心接受盟约。这个信念给父母和孩童双方都提供了力量。在古时,在教会的黄金时代,它曾提供力量,一个荣耀的安慰,其最荣美的果实可以在这个教义上看到:在婴孩时期夭折的盟约孩童必定得救。
神学家们只在阐发这些原则上有不等程度的分歧。人们不得不期待,在每一个盟约成员身上,当他们到达负责任的年纪时,可以看到有意识的转化取用(appropriation),即藉着信心与回转进入盟约的关系里。正如我们试图描绘的,盟约教义的整体倾向会带来这个要求。人们很难满意于这种想法,即只要“不拒绝盟约”就够了,但是却完全没有生命的表现。而这和他们所发现的(也是他们从圣经所知道的),并非所有人都是应许之后裔的这个事实产生了冲突。若对比神学家们在这一点上的说法,显然,在对应许的普遍应用和个体化上,早期神学家显得比后期的神学家更大胆。伯撒(Beza)写到:“由信徒父母所生的孩童,他们的情况非常特殊。在他们里面没有像成人信徒那样的信心品质。但这些生来就被分别为圣,与不信者子女分隔开的孩童,不可能没有信心的种子与胚芽。父母凭信心所领受的应许,也包括他们的孩童,直到千代……若有人反对说,并非所有信徒父母所生的孩童都是选民,正如神没有拣选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所有儿女,对此我们并不缺答案。尽管不能否认情况确实如此,但我们还是要说,这种隐秘的判断应当留给神,正常情况下,基于应许,所有由信徒父母(或父母中一方是信徒)所生的孩童,都被分别为圣了。” (Confessio Christianae Fidei, IV, 48)马提尔大致同意他的观点:“我们不把这个(享受盟约的益处)归因于肉身的出生,当成原则和真正原因,因为我们的孩子得救,唯独是靠神的拣选和怜悯(这经常是伴随着自然的出生)……这不是必然的,因为应许一般不会适用于所有后裔,而只适用于被拣选的后裔……但是,因为我们不可好奇地探究神隐秘的护理与拣选,因此我们假定信徒的儿女是圣洁的,只要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没有显出他们与基督隔绝。我们就不会将他们排除在教会之外,而是接纳他们为成员,并希望他们有份于神的拣选,拥有恩典和基督之灵,甚至接纳他们,将他们当作是圣徒的后裔。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为他们施洗。我们无需回应那些反对者的质疑,是否牧师受了蒙骗,或许这婴孩事实上并不是应许之子,不是神的拣选和怜悯之子。就成人而言,我们也可以推理出类似的讥讽,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带着诡诈而来,是不是真信徒,他们到底是拣选之子还是遭遗弃之子,等等。”(Loci Communes, IV, 8, 7)按照珀拉努斯的说法,信徒的儿女必须受洗:“因为他们是基督的血所买来的,他们的罪已经被洗净了,因此,藉着圣灵的工作,他们拥有洗礼所象征的事物……因为圣灵已经应许给他们,他们拥有圣灵。”(Syntagma, VI, 55)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其他人,尤其是后期神学家的表述则没有这么大胆,而更愿意满足于做出一般性的判断:在信徒的后裔中,总有一个后裔是属主的,对他而言,盟约的诸般应许是有效的,没有任何限制。以海德格尔(Heidegger)为例,他说:“洗礼并非对信徒子女中的每一位,而只对选民印证重生并属灵恩典的全部内容。基于爱心的判断,个别地来说,对他们每一位都心存盼望,这很好,很正当;但集体而言,关于他们所有的人,却不允许我们心怀如此的期盼。”(Heppe, Dogmatik der evangelisch-reformierten Kirche, p. 496)
另一个不同点与这个问题有关:盟约应许借由重生而实现在盟约儿童身上,通常是在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辨识出三种思想学派:第一个学派(包括乌尔辛努斯、珀拉努斯、尤尼乌斯、瓦莱乌斯[Walaeus]、克洛彭博格、威提乌斯[Voetius]和韦修斯)不仅假定达到分辨年龄之前就去世的盟约儿童,在婴孩期之初就拥有圣灵,因此已经重生并与基督联合,而且也坚持认为这种论点对于一切应许的后裔来说都是有效的,没有任何差别。在与重洗派(Anabaptists)的论战中,他们以此为论据,为婴儿洗辩护。乌尔辛努斯说:“毫无疑问,神只为那些承认并持定教会已经是由盟约成员所组成的人,设立了祂的圣礼和盟约印记,祂的意思不是要藉着圣礼使他们初次成为基督徒,而是使那些已经是基督徒的人越来越像基督徒,并且要巩固在他们里面已经开始的工作……因此,若任何人认为基督徒的子女是外邦人而非基督徒,并谴责所有这样的婴孩不能来受洗,他需要小心他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因为保罗说他们是圣洁的(林前第7章),而且神透过亚伯拉罕对所有信徒说,祂要作他们和他们子孙的神……其次他需要考虑,他如何以清洁的良心允许他们受洗,因为故意给外邦人和不信者施洗,是对洗礼的公开滥用和亵渎。当重洗派诉诸婴孩缺乏信心来反对婴儿洗礼时,我们的回答始终是,圣灵重生他们,以适合他们年龄的方式,使他们里面有信靠和顺服神的意愿,我们始终认为,我们放手让自由的恩典和属天的拣选隐秘地工作。”(引自:Südhoff, Olevianus und Ursinus, pp. 633f.)在《大要理问答》中,有一个问题问到:“婴孩既然没有信心,可以受洗吗?”答案是:“是的,信心和信心告白是对成人的要求,除此之外,他们别无他途可以被包括在盟约里。对婴儿来说,只要基督之灵以适合他们年龄的方式使他们成圣就够了。”(问291)比较上文珀拉努斯的引述,其中也涉及到这个问题。尤尼乌斯反驳重洗派,他说到:“我们认为,说婴孩完全不能信是错误的;只要他们有了习性原则意义上的信心(faith in the principle of the habitus),他们就有了信心的灵(the Spirit of faith)……重生可以从两方面看:在“基督”这基石里和原则上的重生;以及它在我们里面发动的重生。前者(也可以被称为是从第一亚当移植到第二亚当里)是根源,后者从中生发出果实。藉着前者,当蒙拣选的婴孩被连于基督时,就得了重生,其印记发生在洗礼中。”(Theses Theologicae, LI, 7)瓦莱乌斯在他针对洗礼的论文中说到:“我们拒绝路德宗的观点,他们把圣灵重生的大能与洗礼的外在之水如此捆绑在一起,以至于这大能就临在于水本身之中,或者至少,重生原则只在施行洗礼的行动中有效。但这不符合圣经在各处所说的,在受洗的人身上,必须先要有信心与悔改,也因此先要有重生的开端和重生的种子……因此,我们不把洗礼的功效和外在的水洒在身体上的时刻绑定在一起,而是和圣经的要求一致——至少是按照爱心的判断(the judgment of love)——受洗者里面先要有信心与悔改,无论是盟约成员的婴孩子女还是成人。因为我们认为,基于神圣的赐福和福音性的盟约,可以确知婴孩里面有圣灵,也有信心与回转的种子。”(Synopsis Purioris Theologiae, XLIV, 27, 29)克洛彭博格反对重洗派的讨论也类似:“我们假定信徒子女藉着圣灵直接而隐秘的工作,已经被连于基督,直到婴儿期结束(无论是在今生或过世的那一刻),以至于(不管是否在肉身之中)他们能够凭信心认信信仰,或得见神藉着恩典所共同赐给他们和我们的。”(Exercitationes, I, 1097)威提乌斯表明,他同意伯格斯(Burges)在原则上的重生(regeneration in principle)与实际的重生(active regeneration)这两者之间所作的区分。他把前者归给盟约父母被拣选的子女,却拒绝伯格斯的立场,说这种原则上的重生跟着洗礼而来,是实际重生的结果。“这不能被他所引用的改革宗神学家所证实。众所周知,按照他们的看法,洗礼的效用不在于引发重生,而在于印证已经发生的重生。”稍早一些,他写到:“第七点是改革宗教师们通常的立场,重生被公认个别地发生在每一个盟约儿童,也即选民身上,无论他们于婴孩期夭折或长大后被带进信仰中,等等。”(Selectarum Disputationum, II, 410-412)最后,韦修斯写到:“我承认,到目前为止,我同意这一意见。”(Miscellaneorum Sacrorum, II, 634)他也认为,这种观点已经被荷兰教会的洗礼常规所接纳。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学派。在这个群体里的人,对于能否对应许儿童重生的时间作出任何规定而犹豫不决。看起来采取这个立场的有詹秀思(Zanchius)、埃姆斯和老弗里德里希·斯班汉(Fr. Spanheim the elder)。但是詹秀思更倾向于认为重生是在洗礼时赐下的,而非远在洗礼之后。他说:“正如一些成人,一些婴孩在受洗之前就被赐予信心的灵,他们藉此连于基督,得蒙赦罪、得到重生;这和那些在洗礼中得到这些恩赐的人,情况是不同的。”(De Baptismo, III, 31, in Commentarius ad Ephesios, Caput V)埃姆斯说到:“我们不否认,神在一些人的洗礼当中将恩典的习性或原则注入在他们里面;但神同样可以在洗礼之前或者之后,赐下同样的恩典。”(Bellarminus Enervatus, ed. 1628, III, 68)斯班汉则说:“洗礼为重生效力。在成人身上,重生发生在洗礼之前,而在婴儿身上,重生发生在洗礼之后。按照神的美意,其生效有时在现在,有时在将来。”(Dubia Evangelica, III, 27, 6)
最后还有第三个学派。他们认为,圣道的宣讲是寻常的蒙恩之道,重生是伴随着蒙恩之道而发生的。他们相信,除非必要,神不会背弃这个原则;对于那些命定要活到负责任的年龄的孩童,要等到他们能有意识地得到所印记的盟约之福时,重生才会发生。伯撒(他在这一点上不总是前后一致)说到:“对于那些生在教会里、被神拣选……和在负责任的年龄之前去世的孩子,我可以很容易根据神的应许,假设他们在出生时就已经与基督联合了。然而,除非是彻底的鲁莽,对于其余的孩子,除了说他们只能在藉着听道而领受真信心时重生之外,我们还能确定什么呢?”(Ad Acta Colloquii Mompelgartensis, p. 106)这一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乌瑟尔,他这样问到:“对于那些被拣选且被神许可成长到可负责任年龄的婴儿,我们应当怎么理解洗礼在他们身上的功效呢?”他的回答是:“如果神的意思是给他们寻常的蒙恩管道的话,在正常情况下,我们没有理由向他们保证,神会做不寻常的工作。虽然神有时候可以在母腹里就使人成圣,就如耶利米或施洗约翰的例子,而其他时候则是在洗礼之时,但我们很难判定(正如有人惯于如此判定),每一位被拣选的婴儿通常是在洗礼之前或之时,领受重生的原则和信心与恩典的种子。而若真有这样恩典的原则已经被注入,它就不可能失落或隐藏到一个地步,以至于无法显明自身。”(Body of Divinity, p. 417)
不过,除了刚刚讨论的这两点之外,所有这些学派都一致同意,将这赐给教会的婴儿洗礼和神的应许关联在一起,意思是从她的儿女中,祂要为自己兴起一个后裔。
[1] 本文译自:Geerhardus Vos,“The Doctrine of the Covenant in Reformed Theology”,收录于:Geerhardus Vos, and Richard B. Gaffin, Redemptive History and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The Shorter Writings of Geerhardus Vos (Phillipsburg, N.J.: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Pub. Co., 1980), p.234-267。脚注省略;文中各级标题为译者所加。
[2] Shibboleth(示播列)一词出自士师记12:6。——编者注
 《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
《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