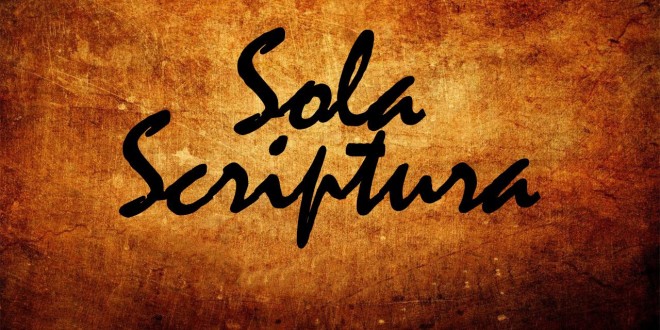文/史普罗(R. C. Sproul) 译/超雪 校/煦
编者按:本文出自史普罗所著《我们是合一的吗?》(Are We Together?),该书是为了回应1994年“福音派与天主教合一”(Evangelicals & Catholics Together)运动,以及2009年一些更正教信徒、罗马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联合发表的《曼哈顿宣言》(此宣言呼吁所有“基督徒”在“福音”里联合起来)。史普罗认为,此运动和这份宣言是他所经历的福音纯正性面临过的最大危机。《我们是合一的吗?》共六章,本文是第一章。本刊“宗教改革纪念系列专刊”将其翻译转载,以呼吁中国教会来关注更正教与天主教的差别,继续坚守宗教改革的立场,传讲圣经里的福音。
当更正教信徒研究罗马天主教神学时,重点通常会放在更正教与罗马天主教思想分歧的主要问题,即称义的教义上,更正教的立场是强调“唯独因信称义”。我会在第二章着手讨论称义的问题,但还有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使得更正教有别于罗马天主教,就是圣经及其权威性。
更正教(Protestant)一词含有对抗(protest)之意,十六世纪的更正教宗教改革之所以被如此称呼是因它在多个方面对抗罗马天主教的教导和实践,但今天很多称自己是更正教信徒的人并不清楚改教家们在对抗什么。
为确定其所牵涉的核心问题,历史学家们通常会指向宗教改革的所谓“质料因”(material cause)和“形式因”(formal cause)。质料因是称义问题,即一个人最终是如何被基督救赎的;形式因是权威性问题,尤其是圣经的权威性,这是根本性的问题,它不处在公众关注中心,但处在整个争论的中心。我们理当从考察罗马天主教对圣经权威的理解入手,并查看其观点与更正教观点有何异同。
在质料因方面,宗教改革的战斗口号是“sola fide”,即“唯独信心”;在形式因方面的战斗口号是“sola Scriptura”,即“唯独圣经”,它主张基督徒最终的、最高的权威只有圣经。
更正教宗教改革最初的推动来自于在德国围绕赎罪券展开的公开辩论。奥古斯丁修道院的一位名为马丁·路德的修士将《九十五条论纲》钉在了维腾堡教堂的门上,引人注目地论述了他所看到的在赎罪券贩卖中的一些恶习,这最初的抗议很快演变成一场与罗马天主教当局在多个神学观点上的、更广泛的对抗。
路德参加了几场与罗马天主教会代表们的重要辩论。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可能是1518年,当红衣主教托马斯•迦耶坦(Thomas Cardinal Cajetan)作为教皇的代表在德国奥格斯堡参加国会(神圣罗马帝国的议会)时,路德在那里露面。在这次会面中,路德陈述了他的观点,就是:教皇在所发布的教谕中的声明可能有错。罗马天主教会是在1870年正式确立“教皇无误论”的,这次会面远早于那个时候。不过,教皇权威的观念在教会内已经被默认了。然而路德敢于挑战这个观念,坚持教皇的教导要被圣经证明。同样地,在以后的辩论中,尤其是在莱比锡与当时罗马天主教会主要的德国神学家马丁•艾克(John Eck)的辩论中,路德否定了教会大公会议的无误性。
历史上,关于究竟在哪里能找到最高权威?是在大公会议,还是教皇的决定?罗马天主教会的神学家们内部有分歧。他们中一些人相信大公会议比教皇的权威性要更高,一些人相信教皇要比大公会议更权威,但路德认为这两者都不是最高权威;他说圣经才是一切的最高权威。他既不认为会议集体决议是无误的,也不认为教皇的个人言论是无误的。
在1521年的沃木斯国会(Diet of Worms)上,争论达到了顶点,当时路德被命令在教会的首领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面前为自己的案件辩护。当要求路德放弃他的观点和著述时,他在思索良久后回答道:“除非圣经和明白的理性证明我有罪——我不接受教皇和大公会议的权威,因为他们彼此矛盾——我的良心是被神的道束缚的;我不能而且不愿撤销任何东西,因为违背良心是不对的,也是不安全的。这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神啊,帮助我!阿们!”[2]
这段陈述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路德对“由圣经判定”的坚持。他视圣经为最终权威。他声称无论是教皇还是大公会议都会并且实际犯过错误,而他把圣经置于二者之上,表明圣经是不会有错的。所以,这个关于圣经的教义立刻被提升为十六世纪所有的更正教团体的核心观点。
高圣经观
因为这场辩论,出现了一幅这样的漫画,使人想到更正教相信圣经是最终权威,而罗马天主教相信教皇或教会是最终权威,这似乎说明罗马(教廷)很轻看神圣的圣经。我想通过考察罗马天主教圣经观的发展来表明这幅漫画并不正确。
天特会议(Council of Trent, 1545-1563)是整个罗马天主教历史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天特会议的召开是为了明确地回应改教运动,它至今仍是关于更正教与天主教争端的会议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在这次大会上,罗马教廷对称义、圣礼和很多其他在改教运动中所争论的问题给出了正式的说明。
在天特会议第四次会议上(1546),罗马教廷详尽地阐述了对圣经的定义:
……从前藉着众先知在圣经中所应许的福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天主之子首先亲口宣扬出来,然后吩咐他的宗徒(apostle,使徒)[3]传给万民,作为一切救恩真理和道德训导的根源;并且明显这真理和训导包括在圣经中,亦包括在由宗徒从基督口中或由宗徒自己传承下来的口头教训中,均是由圣神(the Holy Ghost,圣灵)口授(dictate),并已传承至我们,如同亲手传递一样。(大公会议)追随正统教父的样式,用同样的虔诚与敬重之热忱接纳并尊崇全部新旧约——因为二者的作者是一位天主(God,神)。[4]
在这个陈述中,天特会议宣称圣经是在圣灵口授下,或直接从基督之口,或从使徒那里传给我们的。而且,它称神为旧约和新约的作者。因此,罗马天主教会给出了很高的圣经观。
在这个陈述中最重要的词是“口授”。这里说圣灵口授了圣经的话语。福音派基督徒(evangelical Christians)经常因为对“圣经的默示”(inspiration of Scripture)持所谓“默写论”(dictation theory)的观点而遭到指责,此观点认为圣灵是将圣经的内容一字一词地口授给人类的作者,就好像他是站在使徒保罗的肩头然后说道:“现在写下来,‘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罗1:1)。这个观点限制了人类作者对圣经文本的任何能动性,没有给个人的风格、视角和关切等留下空间。但绝大多数更正教徒是完全反对默写论的。
但因为“口授”一词出现在了天特会议的文件中,罗马天主教的批评者们便说天特会议教导了一种简单、粗陋的默示观。但天特会议并没有详细地说明“圣灵口授”是什么意思。而且,在罗马天主教的学者和历史学家们中有近乎普遍的共识,认为天特会议并不是为了详尽解释关于“口授”的概念。相反,会议只不过是用了一个修辞上的比喻手法来使人注意到这件事,就是圣经以神(特别是圣灵)的能力和权柄为其来源和权威。
如果我们追溯自十六世纪以来罗马天主教的有关圣经的神学发展,我们会看到罗马教廷一直持很强的圣经无误论和默示论观点。尤其是在十九世纪,这一点十分明显,当时因为与所谓现代派(modernist)的论战,圣经真实性的问题对于更正教和罗马天主教两者都成为了焦点。这场论战使得保守的基督徒起来反对自由派神学家,这些神学家致力于攻击圣经见证的可靠性和真实性。现代派的论战经常见诸于所谓美国“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和欧洲及美国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之间。但是,这个论战并不仅限于更正教范围,它对罗马天主教教会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罗马教廷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发布多条法令和教皇通谕强烈地反对现代主义运动。
例如,在第一次梵蒂冈大会(Vatican Council I, 1869-1870)上,罗马天主教会宣称“这些书卷……是在圣神的默示下写成的,它们的作者是天主”。[5]大会决议进一步地说,“它们包含的启示无误”[6],这是对圣经无误性观点的清楚确认。1907年是与现代派论战的关键一年,教皇庇护十世(Pope Pius X)再次重申了无误性的观念。同年,庇护十世发表了两份通谕,都是针对现代主义而再次重申圣经的无误性和默示性,并对现代派的圣经观点进行了严厉地批判。同时,为遏制自由主义潮流,罗马天主教会要求每一个教区神父宣誓效忠教会和她的信条。这意味着那些有着现代派信仰的人必须转入地下或离开教会。
我想描绘的是,在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的头十年,罗马天主教会在圣经论中非常严厉地反对任何自由派倾向,毫不含糊地重申了坚实的圣经观。甚至二十世纪罗马天主教神学中主要的改良派神学学者汉斯•昆(Hans Küng)说,“从利奥十三(Leo XIII, 1878至1903任教皇)时期开始,特别是在现代主义的危机中,圣经的整全性与绝对无误性在教皇的通谕中一直明确地、系统地保留着。”[7]当然,昆个人并不承认无误性,而且他认为教会的宣告是错的,但他以学者足够的诚实来准确地陈述当时教会的教导。
向高等批判开放
1943年,教皇庇护十二世(Pius XII,1939年至1958年任教皇)发表了题为《圣神默感》(Divino Aflante Spiritu)的通谕。这则通谕在近来关于“学者在批判圣经时能拥有的自由度”的讨论中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它对于理解现在罗马天主教会内部对所持圣经观的争论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通谕的开头说到:“受圣神默感,那些圣作者(the Sacred Writer,圣经作者)写成了这些书卷,这是天主在他向着人类如父一般的慈爱中,俯就而赐予我们的,为要‘教训、督责、矫正、教导人学正义,都是有益的,好使天主的人成全,适于行各种善工。’”通谕接着将圣经描述为“天赐之宝”和“有关信仰与道德的教义之最弥足珍贵的资源”。[8]
随后庇护对罗马天主教之前对圣经的教导做了一个有趣的历史性回顾。他承认并同意天特会议的结论,然后加上了一些话:
尽管有这条严肃的天主教教义宣告“全部书卷及它们的每一部分”都具有神圣的权威性,以确保免于任何错误,这之后却有一些天主教作家敢于将神圣的圣经真理仅限于信仰和道德内容,并将其他内容——无论是自然科学领域或是历史领域——视作“附加说明”,并按他们所认为的,视为与信仰毫无关系。在我们记忆中不朽的先辈,利奥十三世,在发表于1893年11月18日的通谕信件《上智之天主》(Providentissimus Deus)中,公平正确地判定了这些错误并用最有智慧的规诫和条例护卫了对神圣圣经的研究。[9]
我想提醒读者们注意《圣神默感》的这一部分,因为庇护回顾了以前的通谕,包括利奥的《上智之天主》,并将任何试图把圣经的默示性和无误性限制于“信仰和道德相关内容”的圣经观定为异端。简而言之,他再次重申了他的前任们所说过的一切。他接下来说道:“我们被研读圣言的渴望所激励,这是我们从教皇职分的起始就继承而来的,认为现在是一个恰当的时机再次重新确认和极力主张由我们的首任教皇所确立并由他的继任者所传承下来的一切。”[10]
他明确地提到了利奥的工作,说:
利奥十三世最首要的关切,是确立了对圣经真理的教导,并护卫它免受攻击。所以,他曾严肃地宣告,凡圣经作者所写的,都是绝对无误的。圣经里的话,无论是论及如天使博士(Angelic Doctor)[11]所说的“按照可感知的方式运行”的物理规律,还是使用比喻,或是使用圣经作者所处时代的术语,亦或用一些现今仍然常用的术语,甚至是一些知名科学家使用的术语,圣经作者所表达的内容,都是正确无误的。[12]
庇护在此表明圣经无误的教义并不表示圣经中没有“形象语言”(figurative language),即我们更正教信徒所说的“现象性语言”(phenomenological language),它是指将事物按肉眼所见的描述出来,比如“太阳绕行在天空中”的这个陈述,这并不是错误。他接着说到对圣经严谨的文本考据和对圣经文本的文学分析的必要性,好使我们可以理解圣经赐给我们时所使用的特定形式。他还说道:
在古代东方作者的言论和著作中,一段话的字面意思并不总是像我们这个时代的著作那样清楚。因为他们所想表达的不是仅被语法和语言决定,也不仅由语境决定;因此其解释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完全从其精神上回溯到那久远的东方时代,并要借助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和其他学科,以正确地判断古代作者们可能会使用的和实际所使用的作品写作方式。[13]
庇护要求人们认真地研究圣经的文学结构,好使我们能理解神的道藉以表达的形式。
这个通谕十分关键,因为它的方向、精神、语言和明确的声明都清楚地表明庇护十二世无意淡化或丝毫地弱化罗马教廷已经做出的对于“圣经无误论”的强烈声明。事实上,他在通谕的开头就不遗余力地表达了他对之前通谕的认同。但因为他在解经原则中允许对文学形式进行分析,罗马教会中的高等批判学者们就得出结论:他们可以自由地考察圣经中的神话形式、传说形式、故事形式以及其他。庇护的通谕打开了一扇恰好容许“高等批判运动”在罗马天主教会内运作的大门。这造成了她自身的危机,并将我们带到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Vatican Council Ⅱ, 1962-1965)。
对无误论的限制?
在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上,罗马天主教会对于圣经权威和关于圣经的教义等问题有很多激烈的争论。在大量的辩论后,大会发表了《天主的话》(Dei Verbum),即所谓《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Dogmatic Constitution on Divine Revelation)。
文中说:“圣经各卷书理当被视为是‘对天主为我们得救的缘故而想要放在这神圣著作中的真理’的坚固、忠实、无误的教导。”[14]大会的保守派一直力争要包含“无误”(inerrancy)一词或“无错误地”(without error)这个短语,他们获胜了。但注意这个陈述中的定语。圣经应被视为在“无错误地”教导什么呢?是“天主为我们得救的缘故而想要放在这神圣著作中的真理。”这不是一个涵盖所有圣经内容的表述。按此表述,圣经无误陈述的唯一主题只有救恩。
罗马天主教会的保守派按照以前教会对圣经的公告来看待《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并说如果罗马天主教是不变的、无误的和系统连贯的,那唯一可能的结论就是《宪章》并没有说什么新内容。罗马天主教已经宣称圣经所说的所有内容都是无误的,这表明其无误性并不仅限于与救恩相关的真理,那些想要把圣经无误性限于信仰和道德内容的人,庇护十二世在1943年发表的《圣神默感》中已经谴责了他们。
在另一面,自由派说《宪章》代表着教会有生机和有气息的生命力的进步。他们相信《宪章》确实是把无误性限定于对救恩的教导,它敲开了《圣神默感》紧紧关闭的大门。他们的立场反映出“梵二”的一些背景,当时维也纳的大主教,红衣主教弗兰兹•金(Franz Cardinal König),宣称圣经在与历史和自然科学有关的内容上有错误。
他强烈地建议大会不要采取僵硬的无误论观点,以致学者们无法批判和纠正圣经在历史和科学方面的错误。自由派认为《宪章》的最终声明反映了金(König)的观点,但教皇并没有明确这个问题,说这要留给后来的世代研究。
所以罗马天主教会的保守派相信关于圣经无误性的问题已经解决;自由派并不同意,主张这个问题依然有待考察。
观点的差异
我详细地进行这番历史回顾是为了表明,从历史上讲,罗马天主教会(至少官方和正式立场)持有很高的圣经观,对圣经十分尊崇。现在我们的任务是:着手于传统罗马天主教和更正教在圣经观上的差异。我想列举两个非常重要的差异。
第一个也是最显著的差异是关于正典的问题。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仅包括归入正典之书卷的数量,还包括确立正典之方法的问题。
罗马天主教圣经包含了一些书卷是更正教圣经中没有的。这些被称为“第二正典”(deutero-canonical)的书卷是指一部分写于“两约之间时期”(the intertestamental period,指从旧约圣经正典结束到新约圣经正典开始之间的几个世纪)的次经。
天特会议将以厄斯德拉上(以斯拉记)、厄斯德拉下(尼希米记)、多比亚传(Tobias)、友弟德传(Judith)、德训篇(Ecclesiasticus)、巴路克书(Baruch)、马加伯书(Machabees)上下卷和其他一些书卷包含在圣经正典中。这些书卷的正典性被更正教所否定。
历史证据十分充足地表明犹太教正典里不包括这些两约间书卷。我也能很确定地说,绝大多数罗马天主教历史学家和圣经学者们都同意历史的证据有利于得出此结论。但这些事实“无关紧要”是因为罗马天主教确立正典的方法。
正统更正教认为圣经正典是“对绝对无误的书卷所做的,可能有误的选择”。也就是说,更正教并不相信教会在正典的形成上是完全无误的。我们相信,教会被呼召在历史上决定究竟哪些书卷属于正典,这些决定是在大量的研究下做出的,并通过了历史的筛选。教会在决定什么书卷被包括,什么书卷不被包括时,有可能犯过错误。当然,那些被选出来的每一卷书卷本身是无误的。因此,就如《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1章5条所说,圣经“足以证明(自证)其为神的圣言,”尤其是由于“圣灵的内在之工,他藉着神的话,并与神的话在我们心中一同作见证”。这意味着我们相信那些在更正教圣经正典中的书卷是“正典”的书卷。
与之不同的是,罗马天主教教会相信圣经正典是“对无误书卷的无误选择”。那意味着,不仅是书卷的写作本身是无误的,就连形成正典的过程也是无误的,教会运用了无误的能力来辨认并分别出了那些无误的书卷。
我们可以这样说明更正教和罗马天主教之间观点的不同:设想神给了我们十本书,其中五本是无误的,还有五本可能包含错误,然后他命令我们去区分并识别出无误的书。如果我们是有误的,我们可能会正确地选出四本无误的,但我们也可能把一本有误的书识别成了无误的。毋庸置疑,我们的决定不会改变书本身的性质。那本没被我们选上的无误的书依然是无误的,虽然我们没有成功地把它放到我们的“正典”里。同样地,我们选上的那本有误的书不会因此就变成无误的。我们的决定不会造成这种效果,因为我们是有误的。
当然,如果我们是无误的,我们将正确地识别出那五本无误的书。我们不会出错,因为我们有无误的能力去识别出无误性。这是罗马教廷宣称其在历史上对于圣经书卷的挑选和收集所具有的能力。
因此,犹太教正典中是否含有某些书卷的历史性问题对罗马教会来说完全无关紧要,因为教会确信她拥有正确的书卷,而这确信又是因为由于她无误的判别能力,她只可能选出正确的书卷。
其次,在圣经上的分歧的核心点是圣经与教会传统的关系。上文我曾提到天特会议第四次会议的决议说:“……从前藉着众先知在圣经中所应许的福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天主之子首先亲口宣扬出来,然后吩咐他的宗徒传给万民,作为一切救恩真理和道德训导的根源;并且明显这真理和训导包括在圣经中,亦包括在由宗徒从基督口中或由宗徒自己传承下来的口头教训中……”[15],所以,天特会议宣称神的真理既包含在形成正典的成文书卷中,也存在于口头传统中。这提出了启示的双重源头(dual-source)的神学观点。但启示是有两个来源——圣经和传统,还是只有一个来源——圣经呢?
更正教的观点是sola Scriptura,即“唯独圣经”,神的特殊启示只来自圣经。其他著作可能具有指导意义,甚至次经虽不是神启示的,对教会也具有益处。但罗马天主教会在历史上承认启示的两个源头,圣经和圣传(tradition)。
这个论点主要与天特会议的决议以及二十世纪在此论点的辩论上所做的声明有关。随着所谓 “新神学”(nouvelle théologie)在天主教会的激进派中的发展,罗马天主教会内部有些人想要摆脱这个启示的双重来源论。希奇的是,这是由一个圣公会学者引起的,当时他在对天特会议的历史背景进行博士论文的研究,偶然间发现了一些重要信息。他注意到天特会议第四次会议的初稿说:神的真理是“一部分在圣经里,一部分在传统里”。这份稿件重复了一个明确的拉丁单词——partim, partim(一部分,一部分)——说明启示是一部分在圣经里,一部分在传统里,这是很明确地说明启示有两个来源。但是最终的文件在说明“神的真理是在圣经里和在传统里”时,并没有用这两个词partim, partim,而只是用了et,即“和”这个词。[16]
问题是为什么会议改变了文件的用词,去掉了“一部分……一部分……”的表达,而使用了“和”这个意义模糊的词?如果神的话是在圣经中“和”在传统里,我们能否说神的真理是在圣经中和在《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里呢?作为一个长老会信徒,我相信威敏告白对基督教信仰有非常准确的复述,其中有神的真理是因为它引用和论述了圣经。但是,我并不认为信条是默示的或是无误的。同样,我相信在一篇讲章和一次讲课中能找到神的真理,但那些不是真理的来源。所以“和”一词可能表明:“在圣经中和在传统里”能找到神的真理,但传统并不是启示的源头。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当第四次会议的初稿出现在会上时,有两名罗马天主教神学家站起来反对“一部分……一部分……”的用法。他们当场就以“使用这种表达将会破坏圣经的独特性(uniqueness)和充足性(sufficiency)”为理由提出反对。就在那时,大会议程因战争被迫中断了,第四次会议的讨论记录也恰好在那一点上结束,所以我们无从得知为什么“一部分……一部分……”这两个词改成了“和”。是大会听从了那两名学者的抗议呢?还是只是作为一个研究分歧留在那里?
J.R.盖泽尔曼(J. R. Geiselmann)是二十世纪中期罗马天主教会中新左派的领袖,他坚持说天特会议上“一部分……一部分……”改为“和”是表明罗马天主教会已经摆脱了启示的两种来源的观念。但罗马天主教会内的一位保守派学者海因里希•莱勒兹 (Heinrich Lennerz)说,这个变化只是文体风格上的,并没有什么神学意义。支持他观点的事实是教会在天特会议之后呈现了双重来源的神学思想,并且启示的多重来源在《人类》(Humani Generis,1950)这篇教皇通谕中出现。所以,这仍是罗马天主教神学中的一个紧要问题。
罗马天主教和更正教的宣言
天主教会的最新教理[17](1995)反映了罗马对于圣经与传统,以及组成正典的书卷这些问题的观点:
“圣传与圣经彼此紧紧相连并相通,因为两者都发自同一的神圣泉源,在某种情况下形成了同一事物,趋向同一目标。”两者都使基督的奥迹在教会内临在并使人受益,基督曾许下要与自己的门徒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第80条)
“圣经是天主的话,因为是在圣神的默感下写成的”。“至于圣传,则保存了主基督及圣神托付给宗徒们的天主圣言,并把它完整地传授给他们的继承者,俾在真理之神的光照下,他们能以自己的宣讲,把天主的话忠实地保存、陈述及传扬”。(第81条)
于是,教会受托传递及解释启示,“并不单从圣经取得一切有关启示之事的确实性。因此两者都该以同等的热忱和敬意去接受和尊重”。(第82条)
宗徒的圣传使教会辨认出,哪些著作应该包括在圣经的纲目里。这完整的纲目称为圣经“正典”,包括旧约四十六卷(若把耶肋米亚及哀歌视作一书则为四十五卷)和新约二十七卷:
旧约四十六卷为:创世纪、出谷纪(出埃及记)、肋未纪(利未记)、户籍纪(民数记)、申命纪、若苏厄书(约书亚记)、民长纪(士师记)、卢德纪(路得记)、撒慕尔纪(撒母耳记)上、撒慕尔纪下、列王纪上、列王纪下、编年纪(历代志)上、编年纪下、厄斯德拉上(以斯拉记)、厄斯德拉下(尼希米记)、多比亚传、友弟德传、艾斯德尔传(以斯帖记)、马加伯上、马加伯下、约伯记、圣咏集(诗篇)、箴言、训道篇(传道书)、雅歌、智慧篇、德训篇、依撒意亚(以赛亚书)、耶肋米亚(耶利米书)、哀歌(耶利米哀歌)、巴路客、厄则克耳(以西结书)、达尼尔(但以理书)、欧瑟亚(何西阿书)、岳厄尔(约珥书)、亚毛斯(阿摩司书)、亚北底亚(俄巴底亚书)、约纳(约拿书)、米该亚(弥迦书)、纳鸿(那鸿书)、哈巴谷(哈巴谷书)、索福尼亚(西番雅书)、哈盖(哈该书)、匝加利亚(撒迦利亚书)、玛拉基亚(玛拉基书)。
新约二十七卷为:马窦(马太)福音、马尔谷(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若望(约翰)福音、宗徒大事录(使徒行传)、罗马人书(罗马书)、格林多(哥林多)前书、 格林多后书、加拉达(加拉太)书、厄弗所(以弗所)书、斐理伯(腓立比)书、哥罗森(歌罗西)书、得撒洛尼(帖撒罗尼迦)前书、得撒洛尼后书、弟茂德(提摩太)前书、弟茂德后书、弟铎(提多)书、费肋孟(腓利门)书、希伯来书、雅各伯(雅各)书、伯多禄(彼得)前书、 伯多禄后书、 若望一书、 若望二书、 若望三书、犹达书(犹大书)、默示录(启示录)。(第120条)[18]
与之相对地,最重要的宗教改革教义声明之一《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第一章就论述了关于圣经的教义,列出更正教圣经的六十六卷书,认为它们构成圣经正典。并第在第3条中论述道:
通常称为次经的各卷书,不是神的默示,所以不属于圣经正典;因此,它们在神的教会中没有任何权威性,只能当作一般人的著作来看待或使用。
在第4和第10条中还说道:
圣经的权威性应当受到人的信服,这权威性并不倚赖任何个人或教会的见证,而是完全在于其作者神(他就是真理本身)。所以,既然圣经是神的圣言,我们就应当接受。
要判断一切宗教的争论,审查一切教会会议的决议、古代作者的意见、世人的教训和私人的经历,我们所当依据的最高裁决者,除在圣经中说话的圣灵以外,别无其他。
就这样,十六世纪一直持续至今的圣经分歧,造成了更正教与罗马天主教二者联合之不可逾越的鸿沟。如果更正教和罗马天主教能够同意唯独只有一个启示的源头,就是圣经(不包括罗马天主教圣经中的次经),那我们就可以坐下来探讨圣经经文的含义。但是自天特会议之后,所有试图在更正教和天主教之间进行圣经讨论的努力,一遇到某个教皇教谕或是会议决议时就走进了死胡同。
例如,在关于“圣经和权柄”的争论中还有一个冲突是关于“个人解经”的,更正教这条教义教导说每个基督徒,他或她都有向自己解释圣经的权利。但是这个“权利”中并不包括曲解圣经的自由。因为在神面前,我们没有错解的权利,与个人解经“权利”相伴的是要正确解释圣经的“责任”,而不是将圣经变成为一块为合乎我一己之见而任意扭转、塑造和歪曲的粘土。
为回应更正教对于个人解经的主张,罗马天主教在天特会议第四次会议上宣布:“为了遏制那些放纵的精神,(会议)决定,在基督教教理论信仰和道德的事项上,任何人不可依赖自己的才能,扭曲圣经以求符合己意,擅自解释圣经,以致违反那圣洁的、为母的教会(holy mother Church)——唯独她有判断圣经真义并解释圣经之权利——直到如今所主张的。”[19]也就是说,天特会议已经宣布只有罗马天主教对圣经的解释是唯一正确的解释。当一个更正教信徒提出一个对经文的解释时,如果它和罗马天主教的正式解释不同,进一步交谈就毫无意义了,因为罗马天主教会直接说更正教是错的。在这一点上教会的传统已被圣化了。
—————————————-
[1] 本文出自:R. C. Sproul,Are We Together? Olando:Reformation Trust,2012,本文为该书的第一章。承蒙Ligonier事工授权翻译转载,特此致谢。——编者注
[2] 马丁路德,引自Roland H. Bainton, Here I Stand: A Life of Martin Luther,Nashville: Abingdon Press,1950, p.144.(这本书有中文译本,罗伦H.培登:《这是我的立场:马丁路德传记》,译林出版社)。培登注明“这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一句并没有出现在最早的印刷品里,但这可能是因为听众当时太感动而没在那时做笔记。
[3] apostle天主教译为“宗徒”,更正教译为“使徒”,由于此部分内容是直接引用天主教文本,因此以天主教风格来翻译,但在第一次出现这种词汇时会在后面用括号注明英文和更正教译法。——译者注
[4] 《天特信经》第四部分,http://history.hanover.edu/texts/trent/trentall.html(2012年3月13日存取)
[5] 《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信条》,三章二十四节,1870年4月——《天主教教义宪章》,第二章,http://www.intratext.com/IXT/ENG0063/_P6.HTM(2012年3月12日存取)。
[6] Ibid.
[7] Hans Küng, Infallible? An Inquiry, trans. Edward Quinn,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1, p.174.
[8] 《圣神默感》,http://www.papalencyclicals.net/Pius12/P12DIVIN.HTM,(2012年3月13日存取)。
[9] Ibid.
[10] Ibid.
[11] “天使博士”(Angelic Doctor)是罗马教廷敕封托马斯•阿奎那的头衔。——译者注
[12] Ibid.
[13] Ibid.
[14] 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文件,Dei Verbum,《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第三章,http://www.intratext.com/IXT/ENG0037/_P4.HTM, (2012年3月13日存取)。
[15] 《天特信经》第四部分,http://history.hanover.edu/texts/trent/trentall.html,(2012年3月13日存取)。
[16] G. C. Berkouwer, Vatikaans Concilie en Nieuwe Theologie,Kampen: JH Kok N.V., 1964,pp.111-13.
[17] 本段天主教教理的中文翻译摘自《天主教教理》,http://www.vatican.va/chinese/ccc/ccc_zh-t-0050.pdf(2017年1月6日存取)。——译者注
[18] All citations of the Roman Catholic catechism are from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Doubleday, 1995).
[19] 《天特信经》第四部分,http://history.hanover.edu/texts/trent/trentall.html,(2012年3月13日存取)。
 《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
《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